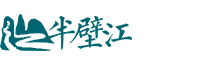|
所有历史都是当代史,这句话说得好。因为过去的人没有机会再书写他们的历史,他们的历史要今人来解读;即便是前人留下了历史著作给今人读,今人一样是用当代眼光来解读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柏杨版《通鉴纪事本末》虽然是一部从春秋到北宋的纪事体通史,更是一部当代史。读此书可谓一举两得,既通晓了古代中国一千多年的治乱兴衰,又可以对当代史学观加以揣摩。
柏杨版《通鉴纪事本末》源于《资治通鉴》。编年体的《资治通鉴》卷帙浩繁,要了解一件事的来龙去脉,就至少要翻上好几遍。司马光后一百年,一个叫袁枢的解决了这一问题,他把《资治通鉴》里有关联的事件都挑出来了写到一起,编成《通鉴纪事本末》。又过八百多年,一个叫柏杨的又以《资治通鉴》和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为底本,编译出白话文版的柏杨版《通鉴纪事本末》,就是当下这套书了。 在我看来,这部书最大的优点就是把历史变成故事。柏杨的白话译文有着柏杨式幽默,并且把传统纪年转换成了公元纪年、给古地名夹注了今地名、给历史事件配了地图、把古代官名换成了今人熟悉的名称。以上这些足以拉近今人和历史的距离,至少使人不再觉得历史仅是个故纸堆。 历史从来都不是一个故纸堆。历史中的无数人事,无不发自于每一个历史人物的起心动念,它们形之于事件,组合成历史。从这个角度出发,使人甚至有一种历史如梦境的感觉。历史总在有意无意之间生成转化,并善于捉弄看它的人。“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看一座山尚且如此,何况是看浩繁多面的历史?
那么看历史看什么呢?正如“所有历史都是当代史”,历史就是一种观念。在古代,这种观念是“道义”,如孔子做《春秋》,历史是其理念的载体;到袁枢那里,他频繁地使用“灭”、“篡”、“寇”、“讨”、“祸”等字眼,就是要表达他的史观;一直到近现代,梁启超仍把“史德”排在“史家四长”的第一位,也就是要以理念统领全局。现在在这部《通鉴纪事本末》既然是“柏杨版”,自然也无可避免地处处打上以柏杨为代表的一部分现代理念的痕迹,比如写皇帝都直书其名,“汉武帝”在这本书就以“刘彻”出现,不能再享受“九五之尊”的荣耀。 一切都是因为,这是一部“现代化”的历史著作。排开文言文的繁难,这部柏杨版《通鉴纪事本末》可以让现代读者轻松阅读,但是也走到了另一个极端,那就是以现代大师的名义,将过往的一切统统推翻,历史不再担当“卫道”责任,而是政治运作与权力游戏的赤裸裸展现。因此,这套书里的历史散发着“腐朽”、“愚昧”和“落后”的味道,充斥其中的是宫廷斗争、官场倾轧——这些可以给今天以实用目的来读史的人以“借鉴”,但是不要忘了事情的另一面:“倾危之士”如苏秦不得善终,玩弄人心者如王莽丧身刀兵,行为某事,必得某果。 这套书对历史是不宽容的。对后世世俗政权的代表人物皇帝直呼其名可以揭掉他们为自己加上的神秘外衣,但是“舜”作为中华文明带有宗教意义的先祖,在这部书也被直呼为“姚重华”,在我看来,这是犯了“过犹不及”的毛病。当然,不仅仅是柏杨,西方那些肩负着现代使命的作家也不例外,比如房龙在《宽容》一书的开头即把现代社会之前人们生活的地方称为“无知之谷”,这正对应了房龙自己所倡导的价值——宽容从来都是个奢侈品。 所以,在读这本书的时候,请不要对历史太苛责。在错综复杂的历史事件之中,其实隐藏着支撑人类社会几千年来绵延不绝的基础价值,比如至为简单的惩恶扬善,比如对义士的赞扬,对和平、大同的向往。现在许多人总是对历史犯有“完美综合症”,一言不合即将之全盘推翻。那没有必要,在新东西没学到之前,盲目抛弃一切只会把人引入事实上的“退化论”——早在半个多世纪前,陈寅恪目睹革命党人争权夺利,军阀混战民不聊生,而有“退化论”之叹。在他看来,盲目崇尚新论而胡乱抛弃中国文化,自我的历史也就蜕化成了一场阴谋和权力的角斗,既然如此,那么现实中道义沦丧,人们的生活只剩下争权夺利,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 最后重新回到本套书,抛开柏杨言辞不论,他渴望中华文化获得新生的心意是人所共睹的,他写到之所以把“范睢漂亮复仇”作为本套书第一册的书名,乃是“象征不但传统历史已获得新的生命,也象征传统文化也获得新的生命”。此话说来容易,在柏杨之前,也有很多人说过类似的话,今后应该还会有很多人讲。然而,上下五千年,大梦谁先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