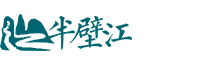|
任何一部历史都是回忆录。在这里,历史是一种过去的时态,我们在对这个时态的确认上不断将发生过的事件按照一定的规律排列上去。它们于是存在,而“存在”本身意味着对过去式的否定,在否定中我们所期待的那个遥远的客观世界才得以真实呈现,而不带上任何的隐瞒或是主观意识的扰乱。对此,中国古代的哲学家曾有过简洁的论述: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这句诗从另一个侧面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具有启发性的经验:历史的再现需要一种分离,分离促成了新形象的奠基线。 奥尔罕帕慕克就是让自己一直处在这种分离的状态下解读伊斯坦布尔的。为此他说他自己从未完全融入过这座城市,他们之间所共有的仅仅只是这其间的呼愁。他为一座城市的呼愁做出了如下的定义:它并非一个单纯的伊斯兰词汇,而是一种象征。在这个世界刚刚形成的时候,地域决定了人类的群种和生存环境,这是一种被动的选择;此后,人们在各自的领地上培养自己的生活习惯,创造自己的文化,并将其局部性地流传下来。我们可以认为,第一代文化的创造者的思想将直接影响到后来成千上万的子孙。奥尔罕于是将处于伊斯坦布尔的文化半径里的历史个性与民族精神(或整体文化与个体性格)之间的共性称为这座城市的呼愁。 奥尔罕通过他的呼愁看见了一座遥远失真的伊斯坦布尔。他看到一个庞大的奥斯曼帝国逐渐熄灭的过程,那久远的忧郁气息瞬间湮没了他。在土耳其这个有着光辉历史的国度里,在伊斯坦布尔的街道或是博斯普鲁斯的海岸,随处可见到繁荣时期留下的废墟。他亦通过四位他所深深尊敬的伊斯坦布尔作家而细致了解了那个王朝覆灭的漫长的过程。人类总是带着美好的实用主义改变他们居住的环境,从而也在无形中造成不可逆转的变迁。当变迁被投放进人的情感世界加以放大时,那么失落感也将被无限加剧。他的呼愁,他的四位作家的呼愁便在于此。 于是当伊斯坦布尔这座城市遭受西方文化和传统文化之间的剧烈碰撞时,奥尔罕的四位作家毕生都企图将这个国家全盘西化。要命的是他们忽略了这个民族自建立以后就一直携带的传统的宗教习俗和文化习惯。因此他们至死都无法实现自己的理想,也为伊斯坦布尔的呼愁加上了沉重的一笔。 时隔多年,奥尔罕对他们保持了相当程度上的尊敬,却并未就此盲目跟从。通过阅读,他似乎更懂得两种文化共存的那种和谐形态的重要性。在《我的名字叫红》、《白色城堡》或《新人生》、《雪》里,奥尔罕莫不是将两种文化间的冲突巧妙地缓和,以诠释当代世界文明多元化背景下的崭新的土耳其文化。他的呼愁的光辉就在于不否定伊斯坦布尔的底蕴环境同时又勇敢承认了外来物质对这座城市的影响。他于是完全融进了伊斯坦布尔,并将诺贝尔文学奖的荣耀带到了这里。 有一段时间,奥尔罕的这种本土作家的自觉性一直启发着我。一个好的作家不在于他完美地描述了什么,而在于他让你联想到什么。我想到我的祖国同样不缺少可以引以为豪的文化资本,却一直难以为世界范畴所承认。在这个国度,当越来越多的文学奖项变成形式主义时,文学就成了一种低层次的自娱自乐。这里的文学比的不是内容而是奖项,于是更多的时候人们醉心于不同立场的谩骂。他们已全然忘记给文学一种宽松的环境,更无从提及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深度去分析和探索这个浮躁社会形成的背后所交织的不同文化体系间的矛盾和冲突。中国同样是个多元化的国家,这样的探索对她的前进尤为重要。我们不需要太过自我的沉溺,而是在迫切期待着中国式呼愁的出现。按照我们的语义,我们可以将它理解成——一种与民族文化相互呼应的忧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