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鲁迅文学院进修时,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同学张新军送我一本散文集《遥远的老房子》。落款签名时间是2013年12月9日。也就是说半年多过去了,我才着手写书评,着实有愧。记忆中清楚地记得,那是在北京午后的阳光里,我阅读了其中的《我的父亲母亲》,读着读着,苦涩的笑和青涩的泪俱现,眼帘浮现出自己的童年和父亲母亲。“我们弟兄几个恨死了父亲,每次挨打以后,都要发誓长大后要把父亲狠狠揍一顿,或者把老鼠药偷偷放进父亲碗里,把父亲毒死!”散文是说真话的艺术。这些文字是浸血的,有着深刻的疼痛。张新军说的是大实话,与我当年的想法何其相似!他对父亲的“恨”不是能用俄狄浦斯情结可以解释的,因为父亲的痛打刻骨铭心。“棍棒底下出孝子。在以后的岁月里,我们和医院结下了不解之缘,天天奔波在医院、家庭、单位之间”。这一中国式的传统教育是否符合国际惯例并不重要,但它的确能起到很好的教育作用。《我的父亲母亲》这篇精美的散文没有美化也没有丑化父亲、母亲,乡下中国式的父母大抵如此,由此可断定张新军虽然在遥远的新疆兵团,但是真实地描述了中国父母、讲述了中国故事、写出了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毛泽东语)。情感流转,笔锋突变,“我的亲爱的父亲,母亲,如果还有来世,我还愿意做你们的儿子,报答你们恩重如山的爱!”由“恨”转爱,终究还是爱,带给读者以心灵慰藉。 在情感波涛滚滚的当口,打算以《诗意中的苦难与坚韧》为题仅就读过的一二篇即兴感怀。但是,通过与张新军近距离接触,发现他很实在,且有内涵。俗话说“文如其人”,于是决定细读整本文集,从而全方位地读懂他、了解他。 半年中,不记得读了几遍文集,单知道这本文集的封皮被翻破了,红色的封皮开始褪色。读着读着不时感慨万千,不时热血沸腾,却苦于不知从何处动笔,说他笔下人物栩栩如生也可,说其中文化蕴藉丰厚也罢,说当中人道主义视野开阔也行,说其间细节过目不忘也中……总觉得值得言说的地方太多太多,所以不敢贸然动笔。 从英特网上搜索后,才知新军在兵团文学中的地位举足轻重,是《父亲的收藏》一文就让他声名远播。此作被《散文》大型文学期刊刊载后,相继被《青年文摘》和《特别关注》等大刊、名刊转载。细读此文,我倒不认为新军的文笔是如何清新优美,语言是如何诙谐幽默,视角是如何别样独到。那么,此文凭什么胜出呢?窃以为,归功于新军的血肉浸染了西部军垦大地。文学素养通天的作者如果仅仅是一个过客,没有像新军那样在大漠戈壁绿洲长时间地生活过、浸泡过,且认真地思考过,是断然奉献不出这么富有质感、有血诚的文字,如《饥饿的菜窖》《排碱渠》《我在连队经历过的厕所》《麻雀群》等篇什都融铸着新军的生命体验,是他用生命与激情书写的兵团故事。再如,《准噶尔盆地边缘》中的这么一段:“我来到童年居住的老屋。家里的大黑狗老眼昏花,已经不认识我了,岁月使它老态龙钟。它一步三晃颠过来,冲我‘汪、汪’两声,声音嘶哑而毫无底气。我小声叫着它的名字,它犹豫了一下,摇着尾巴到我跟前嗅了一会,可能闻出我这个外乡人久违的气味中,还残留着这个年队、这个家的微弱气息,它掉头蹒跚着跑回屋里,给家里人报信去了:家里来客人了!”这些独到的细节颇具生活情趣,但也蕴含几分淡淡的哀伤。如果时间不起作用,如果不是新军生于斯、长于斯,这种细腻的感觉是无法捕捉到的。 说到细节,索性再展开一下(实际上,文集中的细节很多,因篇幅所限,不一一列举)。《我们长在红旗下——校园往事之一》中的一段不可不提:“理发员是一个胖胖的职工,慈眉善目,长了一副菩萨相,一天到晚笑眯眯的。他姓杨,连里男女老少都叫他‘杨地主’,他也不生气。他特别喜欢我们这些男孩子,给我们理完小平头,他每次都用肥胖的手掌在我们后脑勺上猛拍一下,说一声:‘西瓜熟了’。我们的头就理好了,有时我们没带理发票,他就让我们下次带来,下次去的时候,不知是他忘记了,还是不问我们小孩要,他从来不提理发票的事,照例笑眯眯的,照例慢腾腾给我们理发,最后照例是朝我们的头上拍一下,我们给他做个鬼脸,背着书包就跑了。”真正称得上细节的只有“后脑勺上猛拍一下,说一声:‘西瓜熟了’”这几行字,而这个难忘的细节折射出理发师“杨地主”的性格与人品,即乐观、豁达。“文学是人学。”新军选取连队富有代表性的理发师“这一个”来写就是以“点”带“面”。“杨地主”这个典型是整个连队群体中的一个代表,在这个人物身上彰显的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即“仁”。“仁,爱也”(《尚书·仲之诰》)。中国传统道德中的仁学观念,在中国几千年的发展历程中一直绵延下来,新军用文学的方式淋漓尽致表现出来。 由此可见,新军书写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传承的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勇敢地担起了文艺工作者的责任。“后现代的人们,就是一群群流落于传统价值伦理之外的历史孤儿,‘托孤’、‘救孤’、‘抚孤’的历史任务,责无旁贷落于广大作家和文艺工作者身上。作家必须担负起这个历史责任,要用优秀的传统道德故事去鼓舞人,激励人们怀揣美好品德为信仰而献身,让古典的阳光照耀今天卑微的人们前行。”①是的,新军在文本中也佐证了这一段话,如:“当今时代,物质越来越丰富,人的欲望永无止境,而幸福感却越来越低,一些传统的价值观土崩瓦解,所有的一切都标注了价码,包括良心、道德、真理和青春……”(《我们的80年代——校园往事之三》)。 尽管新军笔下的父辈也是卑微的,如《父亲的九月二十五》中写道:“父亲永远生活在社会最底层,蚂蚁一样生活着,但他从来没有失去生活的信心和勇气,即使在最困难最艰苦的日子里,也始终对生活充满乐观而从无怨言。”品着这段话,我自然想到了池莉的《你是一条河》、刘恒的《狗日的粮食》和余华的《活着》。《活着》韩版自序:“作为一个词语‘活着’在我们中国的语言里充满了力量,它的力量不是来自进攻,而是忍受,去忍受生活赋予我们的责任,去忍受现实给予我们的幸福和苦难,无聊和平庸。”上述作品中国人千方百计地“活着”,勤勉、坦荡、坚韧地“活着”,即使活得不是扬眉吐气、滋润痛快,但是,“也始终对生活充满乐观而从无怨言”。这些关乎中国人的故事是沉重的,却是国人生存状况的真实写照,切合中国国情。 卑微的父辈们在艰难困苦中并没有对生活绝望,而是体现了对生活抗争的勇气,因为他们身上蕴藏着一股强大的精神力量,如“父母言传身教,我们从小就知道一切靠自己,靠自己的双手去努力,就像后来父母什么也没有给我们留下,却把让我们立足于这个社会的精神食粮留给了我们,使我们享用终生。父亲一生命运多舛,一辈子与牛羊为伍,他生命中的核心词汇是:准噶尔、车排子、九月二十五、坚韧、执著;他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是:勤奋劳动、永不放弃、乐观坚定、正直向上。物质终归有穷尽,而精神信仰、信心与力量永远是滋养我们成长的心灵鸡汤。”(《父亲的九月二十五》) 2013年12月,中宣部与中国作协等五部门联合发出通知,开展以“中国梦”为主题的文艺创作活动。在实现“中国梦”的进程中,文学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宣传好中国形象,这已成为作家、评论家和文学工作者达成的共识。但是,我发现目前相当多文学作品并没有讲好中国故事。那些所谓的文学作品仅仅是为迎合市场而作,旨在招徕读者,赚取“孔方兄”,里面充斥着血腥、暴力和色情,文学精神消失殆尽。“讲好中国故事,就是要为时代立言,为历史存照,就是要把脚步坚实地踩在这块古老辽阔而又充满沉重忧伤的大地上,与人民同呼吸共患难,当好‘巴尔扎克式的’历史书记官。我们要讲的不仅是《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红旗谱》《创业》《青春之歌》这些励志和创业的故事,我们还要讲《活着》《红高粱》《人生》《活动变人形》《生死疲劳》《蛙》与《笨花》这些饥饿与受难的故事,讲述人民的欢乐与痛苦、天真与庄严、奋斗与倔强,讲述世道的流变与沧桑。我们要通过作品中的文字,让自己的艺术道德理想,构成一个时代精神价值最为深刻最有力度的表达。”②新军的《遥远的老房子》这本散文集中相当篇什讲述了中国故事中饱含“饥饿与受难”。 在苍茫、贫瘠的大地上,父辈们坚韧地活着,自力更生、艰苦创业,让今天衣食无忧却整日怨气冲天的国人们汗颜。 在这个富足而又浮躁、平庸的时代,所谓的散文为了迎合市场正在批量生产。正如法国学者吉尔·利波维茨基在《责任垢落寞——新民主时期的无痛伦理观》中谈到当代新闻时说:“人们不但消费着物品和电影,也消费着搬上荧屏的时事,消费着灾难,消费着现时的及已经逝去的事端,被如此制作出来的新闻,应和着个人享乐主义时代的社会节拍,既如同是一些高度写实的、富有情趣的有关社会日常生活的‘动画片’,也如同是一出让人喜忧参半的剧目。由此,朴素的责任隐没于毫不停息的新闻里,消散在由后道德主义时代的新闻所制作的场景和悬念中。”新军没有消费苦难、展览苦难,而是以智慧的眼光直面苦难。如《我的父亲母亲》中就有令人惊心动魄的对饥饿的感觉体验的叙述描述:“冬季漫长,时光难捱,一家人窝在房子里,粮食消耗得快,常常不到月底,面缸就见底了。父亲在荒野地放羊,侦查好老鼠洞穴。回来后,父亲带着我们兄弟来到荒郊野外戈壁滩,顺着老鼠行走的路线,找到洞穴后,用十字镐掀开坚硬的冻土层,里面是老鼠过冬的粮仓,玉米粒子金灿灿,装到袋子里背回家,洗一洗,放进锅里煮玉米粒子吃。” 我注意到新军在书写苦难时,具有深厚的人类悲悯意识和民生情怀,如《三十亩地》中写道:“这个时代毫无疑问,人人生活得都不容易,特别是像他这种底层人。有时候闲暇下来,他脑海里常常像过电影一样回忆着自己在城市的经历:工地上,他发着高烧爬上高高的脚手架,迷迷糊糊机械干着活,工头还时常无理克扣、拖欠工资。夏日里,他顶着烈日……”。可贵的是悲悯情怀和批判意识在新军笔下达到了高度统一,如“他惊奇地发现,在这个弱肉强食、激烈竞争的世界里,红尘滚滚,物欲横流,有的人良心没被狗吃,有的人良心被狗吃了,有的人良心连狗都不吃!” 《两个乞讨者的午餐》同样如此:“在中国所有城市的大街小巷,都可以看见这样的乞讨者,人们麻木的眼睛已经司空见惯,视而不见,有谁会仔细观察这两个路边的乞讨者的午餐?”如果说有良知的文艺工作者的笔下是悲悯和批判意识同在的话,新军的独到之处是具有浓烈的自省意识和强烈的道德责任感。“我汗颜了,我这个城里人的优越、自尊荡然无存。我与他们,都是这个星球上的公民,凭什么他们衣衫褴褛,流落街头风餐露宿?而我却衣食无忧,优雅度日?他们有何过错?”新军敢于自我解剖,勇气可嘉!再如《我怀念一双琥珀色的眼睛》一文也是如此,正如著名理论家许柏林在《大漠放歌人——读张新军散文》中所说:“野兔之死,经常地强烈地刺激着他的神经,使他忏悔,令他反省,在他的生命与他之外的生命之间产生了血红的融通。” 著名诗人艾青认为:“任何艺术,从它最根本的意义上说,都是宣传,也只有不叛离‘宣传’,艺术才得到了它的社会价值。”那么,《遥远的老房子》这一书则实事求是地讲述了“兵团”在新疆屯垦戍边的中流砥柱作用及“兵团人”的故事,“不溢美、不隐恶”,传承中华民族美德,延续薪火相传的人文精神,其涉及面甚广,包含着作者的追忆、困惑和疑问以及对失落文化的继承与批判。 注释: ①、②徐坤《为时代进步提供正能量》,2014年04月28日《文艺报》第3版。 张友文简介:公安文学推介者、公安文学言说者;自号功不唐捐斋主,笔名碰乡、永伏,鲁迅文学院公安作家研修班学员、全国公安文化理论研究专业委员会(协会)理事、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公安文化研究所特聘研究员,供职于湖北警官学院;出版四部公安文学评论专著:《点击公安文学》(全国首部公安文学评论专著)、《聚焦公安文学》(湖北警官学院院级重点项目)、《盘点公安文学》(湖北教育厅人文社科项目)和《回望公安文学》(全国公安文化发展基金项目和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即将出版);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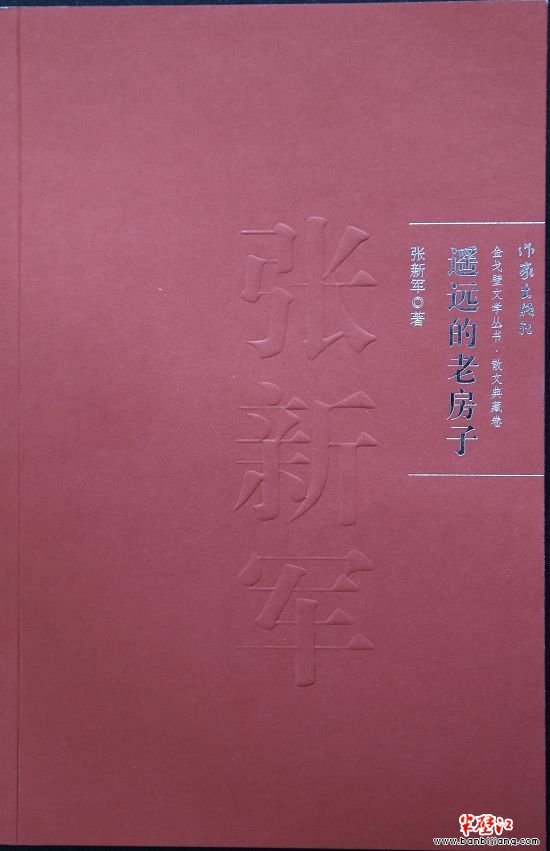

 京公网安备11010202007521号
京公网安备11010202007521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