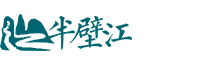|
二三、四十年代围绕着“音”的新诗反省:以歌谣收集运动为中心 1 三四十年代围绕着“音”的新诗反省,当推格律派和“晚唐诗热”,其次有北京大学《歌谣》周刊复刊所标记的北京大学歌谣收集运动的再兴起。 北京大学歌谣征集处成立于1918年2月,四年后成立了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同年12月17日发行《歌谣周刊》(周作人、常惠任编辑),三年共出版了96期,增刊一期,1925年6月28日停刊。1935年恢复北大歌谣研究会,胡适是该会委员。1936年4月《歌谣》周刊复刊。在此我将北京大学民谣征集、研究的历史分为两期:1918年2月至1925年6月的停刊为第一期,1936年4月起为第二期。理由不仅是因为时期上的间隔,更因为两个时期的民谣征集运动之间有相当的区别——第二期显然有了从“音”的角度反省新诗的意味。 第一期由周作人、刘复(半农,1891-1934)、钱玄同(1887-1939)、沈尹默(1883-1971)、沈兼士(1885-1947)分任其事。按歌谣运动的骨干常惠(1894-1985)在《歌谣》创刊号《刊词》中的说法,第一期的目的有两种,“一是学术的,二是文艺的”,“学术的”至少有“民俗学研究”;至于“文艺的”,“从这学术资料之中,再由文艺批评的眼光加以选择,编成一部国民心声的选集。”[33]而且,常惠还认为,“歌谣……就是平民文学的极好材料。……那贵族文学从此不攻而破。”[34]北大歌谣运动的缘起是常惠曾将意大利使馆华文参赞卫太东(BaronGuidoVitale)编的《北京歌唱》(PekingRhymes)送给胡适。常惠认为歌谣有与意大利诗相似的诗法。对新文化运动的这些实践者来说,这意味着他们得到了两个确认。首先,新文化的实践者藉民谣确认了“民间”与“白话文”的关联。换言之,这意味着此一时期的新文化实践者努力尝试从民谣中获取新诗的资源,甚至是白话文的资源,以打通新的“文”与“民谣”甚至“民间”、“大众”之间的关联。周作人在《自己的园地·歌谣》中便说:“民歌与新诗的关系,或者有人怀疑,其实是很自然的,因为民歌最具有价值的特色,是他的真挚与诚信,这是艺术品的共通的精魂。”,另一方面周作人又谨慎地指出有些民谣经“文人润色”的可能[35]。也就是说,“民谣”也未必全都是“民间”或“大众”。显然,周作人也高度关心常惠所说的民谣的“平民性”,但他的“平民性”包含了“真挚与诚信”,亦即所谓“修辞立其诚”(《易经》)这一传统儒家文艺思想的侧面。其次,则是新文化的实践者藉民谣确认了汉语的民谣与欧洲的民谣之间的类似性,继而确认了“中国”与“欧洲”——亦即与作为新的普遍性象征的“欧洲”——之间的类似性关联。朱自清也在其1929-1931的讲稿《中国歌谣》中指出:“这件事(歌谣征集)有多少外国的影响我不敢说。”[36],谨慎地暗示了北大民谣运动与欧洲影响之间的关联。周作人更在《歌谣》一文中援引“意大利人威大利(Vitale)”(上文提到的卫太东)的话“在中国民歌中可以寻到一点真的诗。”“这些东西虽然都是不懂文言的不学的人所做,却有一种诗的规律,与欧洲诸国类似,与意大利诗法几乎完全相同。”[37] 这一时期的北大民谣运动所蕴含的常惠所说的上述“学术”目的外,也附带有以民谣为历史学、民俗学和语言学的材料的学术意图。这一点也可以从周作人的话中得到印证:“历史的研究一方面,大抵是属于民俗学的,便是从民歌里去考见国民的思想,风俗与迷信等,语言学上也可以得到多少参考的材料。”[38]顾颉刚即是一例,他将民谣当作新史料的做法,让人联想起其“新史学”实践者的身份。顾氏在《古史辨第一册自序》(1926)中如是说:“我为要搜集歌谣,并明了它的意义,自然地把范围扩张的很大:方言、谚语、谜语、唱本、风俗、宗教各种材料都着手搜集起来。”[39]他将搜集来的民歌材料用于他的“疑古”,想藉此推翻汉儒和宋儒的《诗经》解读[40]。“我的研究文学的兴味远不及我的研究历史的兴味来得浓厚;我也不能在文学上有所主张,使得歌谣在文学的领土里占有它应有的地位:我只想把歌谣作我的历史的研究的辅助。”[41] 1936年4月起是北大新民谣运动的第二期。这一时期的民谣运动所处的语境与上一时期的民谣运动不同。首先,宏观上看,民谣征集背后固然有完善白话文这一新的书写语言的意图,也有“民族性”这一民族主义的目的,还有与群众相结合这一启蒙和政治的意识形态的动机。而从新诗发展史的角度看,第二期的民谣运动一开始便背负着某种使命:从“音”的角度解决白话文悬而未决的新诗问题。亦即是说,在新诗主张者内部开始出现了对新诗的反省。胡适1936年4月4日《歌谣周刊》第2卷第1期的“复刊词”中显示了这一点: 中国新诗的范本,有两大来源:一个是外国文学,一个就是我们自己的民歌歌唱。二十年来的新诗运动,似乎是太偏重前者而太忽视后者。……我们纵观这二十年的新诗运动,不能不感觉他们的技术上、音节上,甚至于在语言上,都显出很大的缺陷。我们深信,民间歌唱得最优美的作品往往有很灵巧的技术,很优美的音节,很流利漂亮的语言,可以供今日新诗人师法。[42] 胡适总结的新诗来源未包含古典诗歌。对于他那样的新文学激进派而言,这丝毫也不令人意外。但是,如果将这段话看作胡适对过去二十年诗歌运动的反省,就有些令人诧异了。因为胡适的言论隐含这样一种反省:白话文因倚重翻译文学而导致了翻译腔,因而不“民族”或“汉语”,它在“技术上、音节上,甚至于在语言上”有着缺陷。胡适的这一反省似乎不太为论者所留意。但是必须指出,胡适的反省是有限度的,从依然将希望寄托于民谣这一点上看,他二十年来的理念并无丝毫动摇。胡适在这一时期重提民谣,也与三十年代的大众语论争的氛围是不可分的。在上述《歌谣周刊》“复刊词”中,胡适明确指出:“现在高喊‘大众语’的新诗人若想做出这样有力的革命歌,必须投在民众歌谣的学堂里,细心静气的研究民歌作者怎样用漂亮朴素的语言来发表他们革命情绪!”[43] 可见,胡适对新诗的反省表现在他将民谣特权化的主张中。但吊诡的事,他将民谣特权化,则主要表现在将民谣与新诗等同上。这种等同遭到不少批判,尤以胡适的女弟子苏雪林(1897-1999)为最。她在1934年《人世间》第17期上发表的《〈扬鞭集〉读后感》中认为,民歌“粗俗幼稚,简单浅陋,达不出细腻曲折的思想,表不出高尚优美的感情,不能叫做文学。”苏雪林批判自然有简单化之虞。朱自清和梁实秋(1903-1987)则中肯得多。朱自清对“民众文学”持折衷的态度[44],他在《歌谣与诗》(1937年)中说:“歌谣是最古的诗;论诗之起源,便是论歌的起源了”[45],认为歌谣只是诗的前期形态,诗产生于歌谣,但并没有将歌谣等同于诗。这与胡适劲敌胡先驌(1894-1968)所指出的“盖诗者歌之遗”的意思相近[46]。梁实秋基本上也不同意将民谣与新诗等同,但他在《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中客观地认为:“歌谣的采集,其自身的文学价值甚小,其影响及于文艺思潮者则甚大。”[47]可见梁实秋对民谣的观点与胡先驌、朱自清相去不远。 重视民谣与多种意图相涉,从“音”的角度反省“五四”以来新诗,只是与其有关的其中一种意图而已。所谓多种意图,可分别见于胡适及其战友的论点、大众语运动、抗战时期的朗诵诗、五十年代的新民歌运动等,只是不同时期有不同的侧重。显然重视民谣这一行动的意义更多是在文学以外。比如说,民谣的主体多半为妇女[48],因此重视民谣与解放妇女、尤其是劳动妇女的解放有着重要的联系;此外识字率偏低与民谣的发展之间也有关联。这些问题显然又是阶级的问题。胡适说,民谣之“民俗学和方言学研究上的重要,但我觉得这个文学的用途是最大、最根本的。”[49]必须承认,民谣收集运动,与排斥文言文的使命不无关系。而迨至三十年代(第二期),民谣又增加了一个树立“大众语”的使命——民谣等同于新诗的单纯言论出现在三十年代,与三十年代围绕大众语展开的讨论不无关系。 其次,二、三十年代围绕着“音”的新诗反省,最明显的莫过于新诗格律运动。最早探讨新诗格律的是陆志韦(1894-1970),还有新月派诗人徐志摩(1897-1931)、闻一多(1899-1946)和朱湘(1898-1948)。朱自清曾指出:“第一个有实验种种体制,想闯新格律的,是陆志韦。……他相信长短句是最能表情的做诗的利器;他主张舍平仄而采抑扬,主张‘有节奏的自由诗’和‘无韵体’。”徐志摩“却只顾了自家,没有想到用理论来领带别人。闻氏才是‘最有兴味探讨诗的理论和艺术的。”[50]闻一多还专门著有《诗的格律》一书。朱自清的《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以主要的篇幅总结新诗在“音”方面的探讨,可视为从“音”的角度反省新诗的先声。这一时期新诗诗人在“音”方面的探讨,有何其芳(1912-1977)的“顿”、闻一多的“音尺”、孙大雨(1905-1997)和叶公超(1904-1981)的“音组”、林庚(1910-1967)的“节奏音组”和“半逗律”等[51]。三十年代坚持包含格律在内的新诗的音乐性的,可从废名(1901-)、冯至(1905-1993)、何其芳、卞之琳(1910-2000)等人的作品中得到例证。文学史家司马长风(1920-1980)甚至认为,冯至之所以发奋于“十四行诗”,是“对诗的散文化的潮流,多少有冷蔑和抗议的意味,也多少有复振格律的意图”[52]。到四十年代,吴兴华(1921-1966)的“新格律诗”更可以视为从“音”的角度反省并探讨新诗的书写问题[53]。 三十年代围绕着“音”的新诗反省,还有当时出现的“晚唐诗热”。“晚唐诗热”的成员与新诗格律派有重叠,著名者有戴望舒(1905-1950)、卞之琳、施蛰存(1904-2003)、废名、何其芳、林庚等。与冯至从外国诗歌借鉴格律的做法相反,“晚唐诗热”则把目光投向晚唐诗词。但其实质远不止此。两者都是要从(形+音+义),尤其是从其中的“音”的角度,进一步探讨白话文这一新的书写语言中的新诗的可能性。实际上,三十年代的“晚唐诗热”和新诗格律探讨与大众语论争之间蕴含着既对话又对立的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晚唐诗热”可以被看成一场对激进新诗运动的冷静反省,这种反省涉及新诗与旧诗传统的关系,在具体表现上则是从(形+音+义)进而“意”的角度对新诗进行反省,在具体上说又以“音”为切入口。三四十年代关于新格律的探讨,整个可以视为对语言激进主义中的古/今二者择一的进化论文学观的一次反省。 郭绍虞在《新诗的前途》(1941)一文中这样评价新诗格律派从“音”的角度的探索:: 再由格律派而言,更是一种进步。他们也用欧化的句法,有时也用象征的写法,但是重在诗的音节。……此派诗应该有相当的成功,然而仍不为人所注意,易被人忽略过去者,则以创造新音节,较创造新语言为尤难。音节的创造,不能离语言文字的本质。在中国的语言文字里,用双声叠韵,昔人已试验过了;用平仄,更是旧诗音节顶重要的法门。除此之外,舍平仄而采抑扬,讲节拍,未尝不是一条新途径,……何况这又是比较的并不适合于中国语言文字本质的新的尝试!于是有顾到了每行的音步,却没有顾到每行的读,意义的停顿与音节的停顿不一定相符,便不免产生吟诵上的困难。[54] 郭绍虞的议论包含着某种困惑和悲观:新诗书写语言似乎在理论上很难解决“音”的问题。无疑郭绍虞之说也可以理解为围绕着(形+音+义)不可分割的关系而讨论“意”,因为新诗的格律问题显然并非是否押韵这一类表面的音韵的问题,更包含了面对新诗的语言符号时阅读意识的问题。汉语新诗不可能在“音”的层面上孤立地考察,而必须结合汉字这一文字符号的语言学特性与阅读心理的互动关系综合论述。郭绍虞所说的“创造新音节,较创造新语言为尤难。音节的创造,不能离语言文字的本质”,更是洞察了“音”的问题其实是汉语新的书写体派生的问题,换言之,是(形+音+义)中的“音”的问题。 其实,郭绍虞1948年出版的《语文通论续篇》中所收十篇论文中便有七篇探讨汉语、中国文学的声律问题,但其中只有部分文章直接谈到“新文艺的途径”,更多的涉及到古诗,如作者自序中所言,“语言可以决定文字,同时,文字也可以决定语言。语言文字是相互决定的……近来很多人主张语言与文字的协调,以使笔底写出的语体即是口头说出的语言。这种主张不能说错误,而且照这种主张以进行,也很有些人从事这方面的实验而得到成功。但是推广的成效却不能说广。……所以我认为文字不改造,则将来的新文艺虽则是语体,但是可能会形成语文之分。”[55]郭绍虞的意图在于说明言文(语文)一致只能是幻想,即使是新文艺,也不可能是语文一致,文字是不可能为透明的存在。但是,郭绍虞并非否定新文学,而是希望修正新文学易走极端的语言思想。曾受学于胡适,当时又以语言学家、古典诗学理论家渐露头角的郭绍虞其实正是从“音”的角度反省新诗。另一方面,四十年代对新诗的反省依然在创作界持续。“九叶”诗人多为外文、外国哲学专业的学生并非偶然,他们延续了新文学从外国文学中吸取资源的“传统”。同时,文白的距离在他们那里依然明显,意象的浓度在他们的诗作中进一步加强,但是音律的问题却尤待解决。 三,从“音”的反省至“声”的实践:以五十年代的新民歌运动为中心 1 陈子展早在1929年便预言:“二三十年之后,民间文艺将有惊人的进步,尤其是因研究民间文艺的结果,会要影响到整个的文学上的趋向,乃至影响整个的文化问题,怕不是现在的我们所能想象得到的了。”[56]这一说法与前面提及的梁实秋“歌谣的采集,其自身的文学价值甚小,其影响及于文艺思潮者则甚大”之说相类[57]。从以后的发展来看,陈、梁二人可算言中。五十年代新民歌运动与北大民谣运动之间的关联即是有力的证明。其关联在于,两者共同彰显了“民间”和“口语”的价值——在两者看来,从“音”的角度反省新诗,正是在这一层面上。关于新民歌运动的“反省”,正如洪子诚、刘登翰在一本合著中指出的那样,“对于‘新民歌’的高度肯定的背景,显然是普遍存在的对中国新诗地位的怀疑。新诗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是努力证明自身‘合法性’的历史。”[58]。这一看法似被论者所疏忽。 毛泽东于1958年3月22日在成都召开的中央工作会上说:“我看中国诗的出路恐怕有两条:第一条是民歌,第二条是古典,这两方面都要提倡学习,结果要产生一个新诗。现在的新诗不成型,不引人注意,谁去读那个新诗。将来我看是古典同民歌这两个东西结婚,产生第三个东西。”[59]上文已经提到,胡适在1936年《歌谣周刊》的“复刊词”中强调中国新诗的范本有两大来源,即外国文学和民歌,并批评新诗运动太忽视后者。胡适谈的虽是“来源”,所关注的当然也是“出路”,与毛泽东用意差别不大。而且贯穿两者之中的是知识与民众如何结合的道德主义色彩。这一点在毛泽东对文化如何走向大众的设计中表现得更为明显,而且毛泽东本人更是大众与“革命文化”相结合的实践者。但毛泽东的政策自四十年代以来也很快在“民众对知识分子”的二元对立中被演绎为“知识分子的工农化”[60],而非相反。毛泽东的新诗“出路”少了胡适所说的“来源”中的“外国文学”,却多了胡适只字未提的“古典”。但是显然两个人的发言显然都可以解读为对新诗史的反省。 同样是反省,胡适不提“古典”有他坚持“古典”是死文学的立场为背景,他必须自圆其说。而毛泽东不提“外国文学”也许与1956年的中苏论争所代表的反美苏民族主义诉求以及他针对国内知识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反右”运动的动机有着密切的关系。当然胡、毛都有文学大众化的理想,他们共享了这一道德主义立场。在提及“古典”来源这一点上,毛的说法也可视为纠正胡的激进。但必须指出的是,作为相去甚远的“书写”形式,“古典”与民歌如何“结婚”的问题在理论上依然是难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