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来,孔夫子旧书网 “我的专藏”征文活动圆满落幕,说不尽的书话,给我们在盛夏带来一丝心灵的凉爽,且看书友“longkun88423”的藏书故事。 一、开始藏书 我参加工作以后尝试按照自己大学时期的阅读史建立属于自己的藏书,也就是在五年前的那时,我猛然想起Jay Parini说过的一句话,他是美国学者、诗人,也是我非常喜爱的传记作家和书虫,这句话我熟悉得随时都可以写下来,他在一篇文章里这样说“A personal library is an X ray of the owner’s soul”,翻译成中文我就没有太大把握,不过大意是“私人藏书是折射出主人灵魂的X光”。我才恍然大悟,为什么诸多藏家窃据秘本,概不示人,这其中自然有担心对方垂涎觊觎的顾虑,更多的,我想还是对“暴露自己”的担忧。 我就是在这样的帷幕下开始逐步建立具有私人性质的藏书,为了减少支出,即使在经济已经独立的情况下我也尽可能只买自己读过的、喜欢的书。我有自己的标准,我只认可我认可的伟大作品,我知道这对很多杰出的作家不公平,但非常庆幸,我在尚属年轻时就深知人的一生属实有限,实在不宜把精力过多浪费在不喜欢的人、书和事务上面,如此一来,对那些我无缘光顾的好作家我只好在心里道一声抱歉。人书之间,因缘际会,聚散离合,冥冥之中自有安排,诸位深知其味,况人与人乎! 我现在依然清楚记得我是怎样开始接触外国文学中的虚构类作品的。我依着教科书的节选,按图索骥,找到一部很有“党性”的小说,初中,北京燕*出版社,绿色封面,《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按十四年后我今天的看法,译者不好,其它方面也一般。阅毕求教于师,答曰:“故事大概不是真事”,我在听到这句答话的一瞬间很震撼地感受到“虚构”二字的神奇,整本书竟然写得真有其事一般,了不起的是人物之间还有过那么多子虚乌有的对话。 我就这样开始了我的外国文学之旅。 但是,直到很几年以后我才开始注意到翻译家,这时我已经囫囵吞枣看了许多翻译作品,但我还不懂得甄别好坏,所幸我注意到它们的区别了,这是伴随我脑中那个关于“版本”的模糊概念而产生的。我开始先看翻译家再选出版社,也懂得鉴别版本之间的优劣高下,慢慢地我知道了什么是好什么是坏。朱光潜先生说“从翻译中窥外人文物思想,总难免隔靴搔痒”,这个说法有趣得很,接下来他又说“我们的译品太少,而且大半不很可靠”,说得很中肯,我希望自己没有断章取义。后来我一直在想,一个热衷外国文学的读者,除非自己通外语,否则想要读到真正优秀的作品,他必然要经历“选择翻译家”这个阶段。就好比如,年来我身旁的亲朋好友都在劝我该结婚了,他们说“人的一生都有这出戏,晚不如早”。两者道理是一样的。我的朋友这样劝我,我碰到年纪比我大且未婚的,我就拿这句话劝他们!子贡在天有灵,恐亦将“恶”我之“徼以为知”也! 大学开学后我去了沈阳,进了一家全国有名的警校,那时结婚这么遥不可及的事情从来没有提上我的生活“议程”,我用情最多的无非是如何应付高数考试、怎样投篮时跳得更高、怎样摆脱东北让人压抑的冬天。在客居异乡的漫长日子里,我找到了牛顿老师巴罗所说的“温情的安慰者”,我竭尽所能把时间都用在阅读上。大学毕业前我很多次问自己,假如给我一次重来的机会,我会怎样过?我告诉自己,我不会改变这样的生活方式。好吧,现在一切看起来都很美好,很完美,我有难得的精神家园,“中有足乐者”,有几个朋友,也能很顺利投出好看的绝杀,问题出在哪里呢? 买书的钱不够。 二、几本不专的专藏 买书的钱不够,所以我才能清楚地记得当初考虑买方平先生翻译的白朗宁夫人《抒情十四行诗集》时的情景,价格虽然现在看来不高,却也着实犹豫了一阵子。一九五五年七月,方平“试译” 的《抒情十四行诗集》由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出版,进口纸印刷,十六开竖排反开,首印三千册,是月二十日,方平题赠一册给九叶派诗人杭约赫(即曹辛之)、赵友兰夫妇,题曰“辛之 友兰兄嫂留念 方平 一九五五.七.二十”,书名页有“兰”、“辛之藏书”两枚印鉴,末页及书中有“辛之藏书”章,该书经钻孔穿线重装,整体看来十分质朴。刚出版不久的著译者题赠本,藏者多不在意,我倒觉得很重要,“第一时间签赠”,说明两人关系不一般,或者有特殊的缘分在里面,这也是作为读者和藏书家的美国小说家Graham Greene非常苛刻地看重的。
白朗宁夫人 抒情十四行诗集 图/孔夫子旧书网 得到这本书的两年后,我又很偶然得到一本白朗宁,还是方平先生的译本,这是一九九七年六月以《爱情十四行诗集》为名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译文经过修改更成熟,以故初版时的“试译”二字拿掉了,空白的扉页上有方平先生不完整的字迹:“洪风先生雅正 方平 一九”,不知什么原因落款日期不完整,此书一开始多半也没顺利送出去,书名页有先生书写的“自存”二字。也就是在自存期间,方平先生对书内诗文进行了多次改动,计七十七处,几乎每页都有改校的地方。 我曾将方平先生这两本书的照片一起放到微信相册里,配以文字: “几经时岁更替,竟免化为劫灰,披上时光的轻纱,风采更胜当年。继承了威廉•莎士比亚的光荣传统,方平先生早年经意之作,诗人曹辛之藏本,题赠、落款、钤印,不一而足。名家递藏,传承有序,授受之深情,自诗人数读重装之中可见一斑,具有瓦尔特•本雅明所言‘无所不备的一切优点’” 名家递藏、数读重装云云,自然都是我一厢情愿的猜测,我不曾看见诗人动手装订此书,这段文字也只是我愉悦友朋的“戏文”,不过可以看出,我对方平先生的这两本书是喜爱的。 对译文改了又改,证明“好的译者对译文永远是不满意的”,他们对最恰当、最精准的那个表达方式孜孜以求,并且可能终其一生不辍,这两本诗集就是最好的证明。二零一四年一月十九日我又看见了与此册自存本相似的情况,那天下午,我在周克希先生上海的家中看见一堆已经整理好的准备捐献给上海图书馆中国文化名人手稿馆的私人手稿整齐地码在门边的置物架上,征得周先生同意后我翻看了这批珍贵的稿本,其中有一册是周先生翻译的《小王子》。我可以很负责任地说,周译本《小王子》是国内数十种译本中我最喜欢的,我是认真看过其他人的译本才敢说这样的话。我很欣喜,周先生的译本经过多次再版,深得读者喜爱。这本准备送出去的小册子是最早几个版本中的一个,翻开以后我惊呆了。虽然周先生以前告诉过我他的译文是“七改八改改出来的”,我也知道此话一定属实,因我素知他不是一个喜欢吹嘘的人,但听到这样的话也绝不像今天双手捧册亲览那么震撼,八九十页的纸张上布满了不同颜色密密麻麻的修改,有铅笔、圆珠笔、碳素笔,不同的笔还分颜色,每次修改用笔用色都不同,字迹端正整洁,有很好的书法功底,且极富书卷气。二零一三年和二零一四年两个冬天的夜晚,他的《小王子》始终是我泡脚时的必读书。虽然周先生曾说“一个译本能保持二十年已经很不错了”,但我认为他的译文将伴随原著流传下去!那天下午看见周先生这本《小王子》,想起家中那本方平先生的“自存本”,我对周先生提到这本书,他听了以后缓缓地、认真地说:“那应该算是很珍贵的吧!” 二零零八年九月二十九日下午,方平先生在上海逝世,十月七日在龙华殡仪馆举行遗体告别,据说到场的只有不多的几百位,那时我还没大学毕业,没有亲眼看见。 在我的藏书中,第二本给我留下很深印象的题赠本是一九八四年十一月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普希金长诗选》,是书乃译者余振先生题赠林明虎先生,扉页题辞“林明虎同学指正 余振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上海。”,书名页有“林明虎藏书”章。 余先生原名李毓珍,早年是个诗人,后从事译诗,译名较诗名尤盛。先生一九九六年就去世了,因此现在多半不为年轻读者所熟知,但他对俄语文学翻译做出过巨大贡献,这种贡献的余响至今犹在。余先生不愧为俄语文学翻译最力者之一,他也是我很喜欢的著名翻译家王智量先生的老师,余先生翻译的莱蒙托夫影响了不止一代人。作家冰心曾撰文描述她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某个夏天拜访余先生的情景,并在回忆中称自己从余先生的译文中“承受到难忘的恩泽”,写到这里我突然觉得冰心之拜访余振,像极了德国作家黑塞在布伦瑞克拜访诗人威廉•拉贝老人,这两次拜访,都是已成名的作家兼诗人(冰心和黑塞都有一个可能已经被读者忽略的诗人身份)对自己所仰慕的诗人的拜访,最后两个受访者都坚持对来访者送行,唯一不同的是,冰心先生离开时,手上多了一本让我垂涎欲滴的余先生的题赠本《莱蒙托夫抒情诗集》。 虽然伟大的莱蒙托夫曾为不朽的普希金之死直抒胸臆,并对后者致以敬意,以致身受流放之苦,但我不得不十分沮丧地承认,我书架上的普希金先生只配为冰心先生兜里的莱蒙托夫脱鞋!她的莱蒙托夫实在太珍贵了,符合我对完美题赠本的所有幻想。 林明虎先生也从事翻译,但作品不多,“林公”与胡作群、翻译家顾蕴璞等人是北大俄语系的舍友,不知是何原因,几年前林先生的藏书外流(“林公”本身就是藏书家,且家族有藏书传统),光题赠本就有上百种之多,多数钤“林明虎藏书”印,但一开始我只买了余先生题赠的这本普希金,因为那时我正在读普希金,我很单纯地认为能买到余振先生的题赠本来读,是赏心乐事一件。书一到手我傻眼了,哥们的运气来了,我的运气得益于我“大公无私”的工作作风和买书习惯!每得新书我都有检阅的习惯,亚历山大•普希金先生派头再大,来了我照样不开“后门”,先把他的“外套”扒了再说。我就是在这时候傻眼的。一张明信片大小的半透明的横格纸旁若无人地从书衣和封面的夹缝中飘落,我小心翼翼捡起来,看见上面用蓝色圆珠笔写满了字,这些在时光中旅行并等待的字已经被岁月无情地剥夺了一些色彩,因此它们的颜色看起来已经不显得那么饱满、圆润、有生气。我感觉自己如同日本漫画中的小孩进藤光揭开棋盘上的封印以至于无意中释放了寄居棋盘千年的昭和棋圣佐为。 这是一封信。 林明虎同学: 这次去北京,承同学们热情接待,真使我感激莫名。后来想到,送一本小书,以表谢忱,并请留念。但离开学校多年,有的同学,见了面还认识,但名字一时叫不来了。因此,请魏先生给我开了个名单。他不知道你到车站接我去,漏掉你的名字。他告诉后,当然,一定要补送一本。请原谅!祝好! (送你的这本,虽然寄得晚了,但我把错字都一一改正,算是补过吧!) 普通挂号,一走就是一两个月。上次是航挂,这次补送也用航挂,当可于最短期间收到。 大家都好! 李毓珍 85,12,14。 这封信像是现在通行的宝石的证书,有了它,无需验明正身,这本书的来历也就十分清楚了,至于魏先生是何人,我就不得而知了。在这本题赠本里面,余先生用蓝色圆珠笔订正了错、漏、删共二十七处,其中有几处是漏印了一整行诗句,因此这样的题赠本就更加弥足珍贵了。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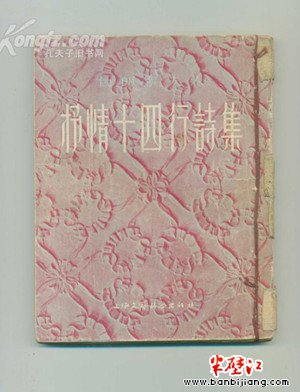

 京公网安备11010202007521号
京公网安备11010202007521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