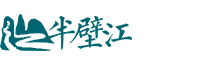|
据科学家提供的数字表明,世界上有30万到100万种不同的细菌,它们中的大部分仍将家安置在泥土之中,以土壤中动植物的遗骸为生,结果是将这些遗骸中的有机物转化为无机物。如果没有这些细菌默默无闻的工作,地球早已经被动植物的尸体堆满。细菌还将植物通过光合作用合成的有机化合物还原为无机元素,供植物循环使用,从而完成生态系统中一个重要的环节。因此,细菌不仅是所有生命的原始祖先,还是所有生命得以继续存在的前提条件。因此,它与人类的关系永远密不可分。 又经过亿万年的进化,大约在距今400万年左右人类出现了。在以后几百万年的人类进化中,除了极少数致病菌有时也会感染人类,但总体上细菌与人类是“和平共处”的。 约在1万年前,人类文明的曙光开始出现,其标志性的变化就是出现了畜牧业和农业。游牧的猎人们开始定居下来驯服饲养动物,人类首次与这些动物发生亲密的接触,于是早已寄生在动物体内的细菌开始侵入人类。大约在6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结核杆菌就已经进入到北非人和欧洲人的肺里。而今天的感冒原来只在马群中流行,大约在4000年到5000年前,由马传染给驯马人,从而开始在人群中蔓延。这时,大规模的问题还没有发生。 后来,城市伴随着文明的进步开始产生,大量的人群往城市聚集,战争和自然灾害的发生,再加上贫苦民众生活在缺乏基本卫生条件保障的环境里,这些都为细菌侵犯人类、传染性的疾病大规模地爆发提供了温床。于是,在某一个临界点上,瘟疫就出现了。 瘟疫一出现,就像一个黑色的幽灵,笼罩在人类的上空,随时把死神送到人们的面前。 我们现在还无法准确地知道,在人类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前,发生了多少次瘟疫,夺走了多少人类的生命。仅凭有记载的历史,粗略地估计,瘟疫夺走的人类生命约在几亿人以上(也有医学史家估计为十几亿人),这是一个多么让人难以置信的数字。 有文字记载的瘟疫,最早发生在公元前4世纪的雅典,距今已有3000多年。 这场瘟疫造成了雅典文明的衰败。 从此在世界历史上,关于瘟疫的记载比比皆是。许多记载甚至是历史学家们自己的亲历和所见。我查阅到的资料上,仅公元6世纪至公元7世纪的200多年里,就有几十次瘟疫发作,而那还仅仅只是记录在案、有据可考的瘟疫。 在公元541年至大约公元750年这段岁月里,瘟疫只不过有潮涨潮落之别,但它从未完全消亡过。在每一个瘟疫肆虐的地区,人口都会急剧减少,并由此产生大量荒弃的耕地。 从1348年开始,一场名叫“黑死病”的大瘟疫,开始肆虐整个欧洲。这场瘟疫让整个欧洲失去人口多达2500万,是欧洲的人口差不多减少了三分之一。 而传播这场延续了几十年的瘟疫的根源,竟是老鼠身上的小小跳蚤。今天医学上称其为“流行性淋巴腺鼠疫”,因患者身上常常会出现黑斑而被称为“黑死病”。 到了17世纪中叶,“黑死病”就像它无声无息地到来一样,又悄无声息地消失了,消失得无影无踪。 我们不要以为“黑死病”只是在欧洲,它离我们很遥远。 从1894年开始,它又突然出现,一直持续到20世纪中叶。许多鼠疫专家认为,这次流行是从中国广东和香港开始的,到1930年达到高峰,到50年代才基本停息,波及亚洲、欧洲、美洲和非洲的60多个国家。 近代随着航海业的蓬勃发展,海船把瘟疫带到世界各地。当代航空器的进步,人们已经能在24小时内飞到地球的另一边,也能把任何一种传染病菌迅速地带到四面八方。 人类的历史即其疾病的历史。疾病或瘟疫伴随着人类文明的进程,并对人类文明产生深刻和全面的影响,它往往比战争、天灾来得更剧烈。因为它直接打击了文明的核心和所有生产力要素中最重要的人类本身。 人类文明的历史摆脱不了传染病的纠缠,人类与瘟疫进行着不屈不挠的斗争。 20世纪30年代化学家们发现了磺胺(含有硫黄的合成物)对治疗细菌感染有惊人的效力;40年代以盘尼西林(即青霉素)为代表的一批抗生素出现,它们所表现出的杀死致病菌的神奇功效,使人们终于对彻底战胜传染性疾病充满了幻想。当时美国甚至有卫生官员公开宣称:我们离摆脱传染性疾病纠缠的时候不远了。 近年来,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特别是电脑网络和基因工程的迅速发展,人们对自身的力量更是充满着自信,我们已经渐渐地将瘟疫伤害人类的历史淡忘。 可是,近些年来,一些非常奇怪的疾病,一些人类还未能认识的传染源,不断地出现在我们身边。一些清醒的医学家们也在不断地发出警告:“瘟疫流行的时代并没有离我们远去”。但这种声音没有唤起人们足够的重视。 所以,当广州中山二院的黄子通,为弄明白苏姓患者可疑的死亡原因而四处奔走的时候,他心里就有一种不祥的预兆。 当我正在阅读和思考的时候,并非耸人听闻的事就在我们的身边悄悄地发生了。一种黑色幽灵侵袭了中山二院,进而侵袭了整个广州。 这个黑色幽灵,后来我们把它叫做“传染性非典型肺炎”,简称“非典”。世界卫生组织把它叫做“SevereAcuteRespiratorySyndrome”(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简称“SARS”。因我用母语中文写作,为维持文体的统一和文字的纯粹,文中我将其统称为“非典”。 “非典”全世界才感染了8400多人,死亡812人。因此,远不能说是一场瘟疫的流行。但是2003年的春天,地球上最智慧的生物(有着计算、通讯能力和创造性的人)与最简单的生物“非典”(只是一小段核酸,甚至不能称为一个完整生命的病毒)发生了一场战争。这场战争人类取得了初步的胜利,但是也许我们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无法取得像人类战胜天花那样的彻底胜利,因为,我们还无法彻底消灭已经产生的这种变异的“冠状病毒”。 于是,作为一名记者、一位报告文学作家,我知道该出门了,尽管满世界都是口罩。那天,我离开家之前对妻子说,我要去广州。妻说,广州“非典”闹得那么凶,人家躲都躲不及,你还往广州跑干什么?我说,我就是为了“非典”而去的。妻不解地望着我。我解释说,我要去采访抗“非典”。妻子沉默了一会儿说,不能不去吗?我说,不能。说完我就出门了。 这么多年来,从事报告文学的创作,我写过许多大案要案,也曾在1998年抗洪中趟着齐腰深的江水去采访。前两年为采写有“世纪大盗”之称的香港黑社会头子张子强,我多次独自去香港、澳门,妻从来没有担心过。但是,这一次她心存深深的担忧。为什么?因为面对着的“非典”病毒,我们不知道它在哪儿,又会何时攻击我们。 但是我走了,背着一个简单的行囊,从发现第一例“非典”病人的佛山,一步一步地走去,一直走进遭受“非典”重创的广州。这一走,等我回到家中,已经是42天后了。 这一切都源于那个必须要在电子显微镜下放大万倍,才可以看见的变异的“冠状病毒”。 这个“冠状病毒”给我们带来了什么? 中国第一例回顾性发现的“非典”病人 我来到广东省佛山市的那一天,是一个阴雨天。 佛山在广州的西南约16公里处,我从广东省卫生厅出来直奔佛山,车程也就半个多小时,但在佛山城内寻找佛山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简称疾控中心,国际上简称为CDC),却用了差不多一个多小时。由于对“非典”病毒几乎是一无所知,我在老城区那潮湿陈旧的街道里穿行时,心里有一种怪怪的感觉:为什么最早的“非典”病人在这里出现? 雨,渐渐地下大了,我站在老街上那经年累月的老榕树下避雨,雨水顺着树叶滴到我的脸上,一股冰凉冰凉仿佛有点刺入皮肤的感觉,我下意识地跳了出来,好像那沾满尘土的雨水会带着“非典”病毒侵袭我。 佛山,是一个有着1300多年历史的古老城镇。“非典”和古老有关系吗? 2003年的春天,是一种什么样的“病菌”偷袭人类,在佛山那陈旧的老城中,我开始寻找答案。 佛山市疾控中心在老城区那错综复杂的小巷内,我在普群南路找到那幢小楼时,已是中午12点18分。 所谓“疾控中心”就是过去人们所称的“防疫站”。中心主任黄祖星正在办公室里等我。我们都没有顾上吃饭,就开始了采访。 随着黄祖星的介绍,在我的面前展开了中国第一例回顾性的“非典”病人出现的情景: 2002年11月16日晚,佛山市禅城区张槎镇弼唐乡有一位庞姓乡干部突然感到浑身发热,周身不舒服,一开始以为是一般的“感冒”,并没有怎么在意,吃了点感冒药就又睡下了。第二天,症状有点减轻,庞先生在镇上负责物业管理工作,他仍然坚持去上班去。但接下来的几天,“感冒”症状却越来越重,体温也越来越高。 11月20日,庞先生在家人的陪同下,就近来到了佛山市石湾区人民医院就医。医院已开始怀疑他是伤寒,后又把他当做由消化道感染引起的恙虫病来治疗,给他服用了一些常规的抗生素。但是,病情并没有减缓。当时,庞先生就住在普通病房里,没有采取特别的防感染措施。曾护理过庞先生的一位护士说:当时几乎没有一个人戴口罩,但没有一位医护人员被感染。 (责任编辑:冷得像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