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南京作家丁捷似乎是“写作成就人生”的典型范例——14岁发表处女作,17岁开始获各种写作奖项,因写作特长而入选“中华杰出少年”,免试进入南师大中文系,毕业后当过大学教师、省级机关干部、省属企业集团负责人,并援疆三年。写作为他打开广阔世界的大门,丰富的人生经历又给予他写作灵感。从中短篇小说到长篇小说、散文、非虚构写作、诗歌,他并不局限于某种写作体裁,而是一直在探索各种的可能性。在丁捷的作品中,既有个人爱情,也有奉献社会的大爱,还有对生命的思考与追问。日前,他的小说《依偎》获“亚洲青春文学奖”,作品在彻骨悲凉的氛围中,探究爱情的极致。 记者:《依偎》中对于感情追求的纯净和极致,也是许多人可望而不可即的,可否谈谈这部作品的创作背景与初衷? 丁捷:“中国人缺失灵魂”——这句批评几乎成为当下的口头禅。我们现在很焦躁,我们的灵魂被关在世俗的笼子里。我们被功利时代泛起的多重雾霾淹没了,只顾拼命地挣扎,实在无暇擦洗内心。一个倡导了几千年温良恭俭让的国家怎么变成这样?华夏子孙很容易成为行尸走肉吗?我想未必。有一阵子,我老在琢磨以上这些问题。 我写作《依偎》的那几个月,南京和全国许多城市遭受了沙尘暴,电脑的键盘若不每天清理,就是一层垢;同时,我们这个城市在炮制一档“非诚勿扰”秀,万人空巷大讨论宝马车里哭和自行车上笑。我想再洁癖的东西在这种环境里,都无法洁身自好。所以,我进入一种“真空”的写作实验———一个叫亚布力思的地方,白雪皑皑,毗邻一个叫藤乡的乌托邦,两个在世俗里受伤的心,在这里结伴,碰撞,纠合,一起去寻找和修复彼此的青春。最终,灵魂闪现,他们进入真爱天堂。《依偎》的目的是展示灵魂的强大,昭示生命的光辉。我们的灵魂在深处,在远处,越高贵则越隐逸。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寻求。可能这也就是我的写作方向。 记者:在阅读中,对《依偎》印象最深刻的并非主线爱情,而是对两位主人公各自前半段人生的复述,这一部分的刻画细致入微。在几部广泛流传的作品之外,您在包括《现代性诱惑》等在内的中短篇小说中也呈现出对于生活感受纤毫毕现的特质,因此也有人说您的作品对生活是一把精准的“手术刀”。这样的感受,是与生俱来,还是源于生活历练? 丁捷:如果简单从题材看,出于生活经验的小说只有《亢奋》。这部长篇小说有将近40万字,是目前为止我最长的一部小说。这部书在新浪等读书频道上线后,创下了多个网络阅读排行榜前十甚至第一,还作为网络文学获得紫金山奖。热闹了一阵子后,我冷静了下来。我觉得自己对现实并没有深度把握,开的不是潜艇,而是花哨的滑翔机。这不是我的本意。“亢奋”这个系列我终究会写,但不是现在,是若干年后。太近的生活,非常需要沉淀。正在经历的生活绝对比不上回顾的生活。 我是一个有反思生活和自我强迫症的人。我静下来的时候,除了阅读写作,大多数时候就是在那里“卖呆”———我的心海中潮涨潮落,翻腾不止。过往生活、他人和我自己,以及附着的情感,一一走台。我的内心,远不似我这个大男人这般看上去平静、无趣。 记者:在您多年的写作经历中,散文短章、非虚构作品以及诗歌等方面的创作一直穿插在小说创作的过程里,并且有如《沿着爱的方向》《约定》 等多种体裁的佳作,虽然并非全职写作,却一直保持着“高产高质”。 丁捷:文学是我们这一代作家的宗教。读书写作于我而言,就如同教徒在做祈祷做礼拜。而全职写作在我看来就如同一个信徒,为了他的宗教直接剃度出家了,这我不能接受。我更愿意让我的身,行走在生活的庞杂里,让我的心,跳动在自我的热血里。文学是我的一种心灵修为,跟我从事的一切正当的世俗职业都并不冲突,至少不是非此即彼吧。 记者:单以“小说家”、“青春文学作家”等称谓来定义您显然并不合适。而一些作家在跨界写作中所产生的习惯性紊乱似乎在您的作品中难觅踪迹。包括从《缘动力》,到《约定》,再到《依偎》,这些作品中,您所呈现的是完全不同的写作姿态,是否可以就此判断,您关注更多的是写作本身以及借由写作来倾吐的感觉,而并非某种擅长的文体或写作风格? 丁捷:我的写作关注更多的是写作本身以及借由写作来倾吐的感觉,而并非某种擅长的文体或写作风格。我是庞杂的,我喜欢一种汪洋恣意。往往是,一旦进入写作,我就被某种情感,某种内容,所俘虏所驾驭,对于我最初的构思,我常常是失控的。文章本身如孩子,为自己所生却不完全属于自己,更不可能要求在抚养他们的过程中,设计他们的一招一式,要允许其自我发育,形成自己的独到个性。 记者:很多年以来,由于青春文学写作热潮的影响,许多读者对于青春文学的印象停留在校园故事或懵懂恋情上,但在您此次获奖的作品《依偎》中,青春文学已经脱离了“青春期感受”这一语汇,转而用回溯、挖掘、织补伤口的方式填补每个人都曾经历的多种情感隐痛。对于“青春文学”这一定义,您显然有着自己的理解,可否就此谈谈? 丁捷:许多概念都是事后诸葛亮总结出来的。我写作《依偎》的时候,压根儿没有想到要写一部青春文学,我也不认为《依偎》可以用“青春文学”来概括。但我不反对给文学作品贴标签,因为这有利于提醒某一个读者群体,某些作品更适合他们的口味。文学归类的事,我建议作家不要做,甚至文学研究者都不要做。书商可以做,贴个标签可以营销,可以分类推荐。读者也可以做,划分类别利于自己系统地有针对性地选择阅读。 记者:在许多国家,青春文学也有“畅销书”的归类,但在文学创作中,许多作家有意识地将注意力投射在更广泛的社会背景下,并为作品赋予了更多涵义。但就我们国内的阅读范畴中,作家们对于青春文学的创作意识多集中于对于懵懂恋情的描绘或残酷书写上,且大量存在着“站在成人立场想当然地幻想青春”的弊病。 丁捷:如果一想到青春,就写懵懂恋情与残酷,那应该是儿童文学思维。“青春文学”是往儿童文学靠呢,还是往成人文学靠?抑或青春文学就是青春文学?其实,怎么靠都有问题,对于作家,不要想这回事。当下“青春文学”已经不是一个好标签,大量文学商人的蜂拥而至,淹没经典,挤垮真正的文学市场,使一代一代的孩子正在受到误导。青春和文学,是不可以当做消费品的,就像教育不应该产业化一样。我常常杞人忧天,认为这是母语的劫难,长此下去,中国文化和人心,就无法高而尚,粹而美。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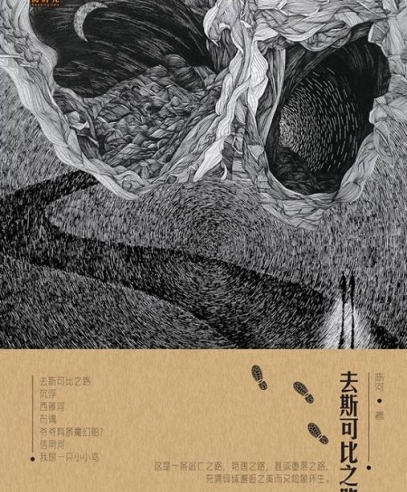
 京公网安备11010202007521号
京公网安备11010202007521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