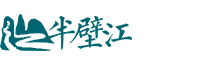|
最古老的文学杂志《格兰塔》中国行主编在沪接受早报专访
《格兰塔》:一本专注于主题的文学杂志
《格兰塔》于1889年由剑桥大学的学生创立,杂志名字取自于附近一条河流。1970年,《格兰塔》因为资金等原因停刊,直到1979年才复刊,并专注于编辑“主题书”。作为一本季刊,它一年有4个不同的主题,每期主题从个人体验到公共政治话题均有涉猎。最近几期主题包括“恐惧”、“十年之后”、“巴基斯坦”等。

《格兰塔》现任主编约翰·弗里曼(John Freeman)

副主编艾兰·奥芙瑞(Ellah Allfrey)

1979年秋季,复刊后第一期

2007年冬季,第100期特刊

2011年春季,“外星人”主题
“在它对回忆录和图片新闻的融合中,在它对当代现实主义小说的推崇中,《格兰塔》将面庞紧贴着窗,决意要见证这个世界。”英国《观察家报》如此评价这份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学杂志。从1889年诞生于剑桥大学至今,《格兰塔》(Granta)已经有120多年历史。它没有政治或是文学宣言,但是坚信故事讲述的力量和必要性,无论是小说或是非虚构类文学作品,故事都具有描述、启发、让梦想成真的至高无上的能力。
11月18日至20日,《格兰塔》现任主编约翰·弗里曼(JohnFreeman)和副主编艾兰·奥芙瑞(EllahAllfrey)来到京沪两地,代表杂志首次与中国同行和作家交流。11月19日在上海短暂停留一天期间,弗里曼和奥芙瑞接受了早报记者专访,谈及这份杂志的运营情况、杂志与文学的关系。
在采访中,弗里曼同样提到了故事讲述的重要性,他说,《格兰塔》的长处来自叙事。“我相信叙事的力量,它是美的,是我们叙述人生的最重要工具。在我们的想象中,我们的生活是故事,我们国家的历史是故事,这就是我们的出发点。”至于文学杂志的价值,就弗里曼看来,在这个没人愿意冒险的时代里,它仍有存在的必要,因为“它能让作家去冒险、创新,而不用去考虑市场”。
文学刊物谈政治要有故事
东方早报:你们是如何确定每一期的主题的?
约翰·弗里曼:我们喜欢有多种含义的那些主题,创意随时都有,有时候是无中生有。比如“巴基斯坦”主题,就是小说家彼得·凯里建议的,他是我们杂志的特约编辑。“芝加哥”主题是因为我在芝加哥开写作会议时突然想到:有多少聪明有趣的美国作家是从芝加哥来的啊,再加上美国现任总统又是从那里来的,这整个城市又在变化中。“恐惧”这个主题是我们一个编辑的15岁侄子提议的,我们也找到了斯蒂芬·金。
东方早报:《格兰塔》的文学主题中涉及政治议题的非常多,你们希望自己的杂志在多大程度上介入政治?
约翰·弗里曼:在我看来,要写出兼具政治性和文学性的作品是很难的。我们不反对这类作品,只是觉得这样写风险很大,这样的作品也很难找。
艾兰·奥芙瑞:我觉得这和对作者的选择也有关系。假设我们以战争为主题做一期杂志,如果我们没有好好挑选作者,那期杂志很容易就会传达出好战或反战的态度。但我们没有这么做,我们刊登的都是反思性很强的作品,它们让人思考:我们在做什么?我们是谁?这一切有什么意义?我同意一切都是政治的说法,可我们不是一本时事杂志,报道时事是报纸的任务。但我们也想探讨这些问题,探讨的前提是一定要有故事,即便是非虚构的文章,也要有关于人的故事。
东方早报:说到政治,《纽约客》或《纽约书评》也会有很多内容是涉及政治讨论的,你们的差异在哪里?
约翰·弗里曼:《纽约书评》很政治,涉及内容都是现在的事、现在的政治,它是要改变社会。比如在布什执政时期,我们对美国政府的作为感到十分困惑迷茫,军队滥用武力、刑讯逼供,《纽约书评》对这些事情都做了记录分析,对美国文化做出了重要贡献。至于《格兰塔》,它的长处来自叙事。我相信叙事的力量,它是美的,是我们叙述人生的最重要工具。在我们的想象中,我们的生活是故事,我们国家的历史是故事,这就是我们的出发点。
艾兰·奥芙瑞:比如我们的“巴基斯坦”专号。我们西方人在想到巴基斯坦时,多数人联想到的都是恐怖主义、人民水深火热的生活。但等我们请巴基斯坦作家写自己的生活,他们写出的却是爱情故事,他们关心生活中许许多多的方面。要说政治,他们的确是在写政治,也触及了眼下的种种斗争,但他们主题不单调,通过这些作品,你可以看出作家在思考“我是谁”,在探索自己的身份。
《格兰塔》从没赚过钱
东方早报:你们在和《收获》等几位杂志编辑交流的时候,都表示很羡慕中国文学杂志的发行量,对《收获》等杂志几万份发行量而且可以盈利感到非常吃惊,你们现在的状况如何?
约翰·弗里曼:我们没有一年赚过钱,实际上亏了不少。我们收入的60%来自订阅,20%来自书店销售,10%来自报摊销售,还有10%来自海外销售。
东方早报:那你们怎么生存?
约翰·弗里曼:《格兰塔》最近被一个瑞典慈善家收购了,他就是喜欢我们杂志的风格,他希望这个杂志能很好地生存下去,所以愿意给予很大投入。
东方早报:他喜欢你们杂志,又投了那么多钱,那他会干涉你们的编辑工作吗?
约翰·弗里曼:他非常喜欢这个杂志,也希望杂志能一直保持原有的风格和优势。我知道编辑杂志非常困难,经常会受到各种干扰,比如我有一个朋友也是编辑,为了选题,他要说服12个董事会成员。还有一个朋友的杂志属于非营利机构,所有成员都是志愿者,结果导致错误率很高。但我们的老板不会干预我们工作,这是我们幸运的地方。
东方早报:很多杂志都开始接受网络订阅,你们现在可以吗?
约翰·弗里曼:我们以前没有网上订阅,后来我们发现有越来越多人会到网上浏览,所以我们对网站进行了改造。而且订阅了《格兰塔》,就能在网上看过刊的内容。
做文学杂志要保持好奇
东方早报:在这个互联网时代,为什么还需要文学杂志?
约翰·弗里曼:文学杂志可以定义什么是新的文学。现在的出版商已经不再敢冒险,一位作家接连几本书卖不好,出版商就可能不再愿意出版这位作家的作品。但是,有些作家要写五六本书后才可能有好的作品。文学杂志的重要性就在于,让作家去冒险,去展示一些新的东西,也可以让我们了解新的作家。
东方早报:你们如何说服成名作家去写符合你们主题的作品?
艾兰·奥芙瑞:作家都会经历一些阶段,一开始雄心勃勃,尝试各种文体,做各种实验。我也愿意找这样的作家。有一些作家在成名后不再写早期作品类型,也不能指望作家一直帮你来写小说。而且特定主题是有风险的,你不知道最后呈现的样子是什么样的。但作家总会碰到不感兴趣的主题,比如A.S.拜亚特一直很抗拒写回忆录,但通过电子邮件沟通后,她还是愿意写的,最后写了篇非常好的回忆文章。
约翰·弗里曼:约稿过程中,50%是运气,50%要揣摩作家的心思。
东方早报:《格兰塔》的长处还在于挖掘年轻作家,你们是怎么发掘的?
约翰·弗里曼:有的年轻作者是参加写作计划出道的,在爱荷华、斯坦福、密歇根都有这样的计划,他们把作者作品寄给我们,希望我们能出版。因为《格兰塔》的声誉,许多作者都会把他们认为达到发表标准的作品向我们投稿。我们也跟文学经纪人合作,他们很善于发现有才华的新人。
艾兰·奥芙瑞:文学杂志的一个危险的地方是:可能会变成一座博物馆。而好的做法是走到外面的世界里和人交流、寻找新作品。例如现在的许多出版社都对投稿设置了苛刻的要求,但我们杂志是有稿必阅的,我们不会高高在上,完全依靠经纪人给我们找作品。我们会走出去,和许多人交谈、读许多作品、寻找在外国出版作品的作者。我觉得做这行你要保持好奇,要去寻找新的作品。
(责任编辑:冷得像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