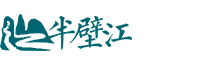|
我听见我们扔出的石头/跌落/玻璃般透明地穿行岁月/深谷里/瞬息迷惘的举动叫喊着/从树梢飞向树梢/在比现在更稀薄的空气中静哑/像燕子/从山顶/滑向山顶/直到它们沿着存在的边界/到达极限的高原/那里我们所有作为/玻璃透明地/落到/仅只是我们自身的/深底
上面这首简练而耐人寻味的诗来自瑞典诗人托马斯·特兰斯特勒默。刚刚过去的一周,瑞典文学院宣布,将2011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这位已经80多岁的瑞典诗人。对于这条新闻已经有无数的解读,比如这是1974年以来瑞典人再获诺贝尔文学奖,这也是1996年以来诗人再次获奖,这也是诺奖再次回归自己的“欧洲中心”和“理想主义”原则。
但特兰斯特勒默的得奖被认为是无可争议的。自上世纪60年代起,他陆续发表的诗集,就在同代抒情诗人中奠定了领先地位,被译成数十种文字出版,成为最受欢迎的当代斯堪的纳维亚诗人之一。西方评论界一直认为特兰斯特勒默是“当代欧洲诗坛最杰出的象征主义和超现实主义大师”,他的诗是凝练艺术的范例,擅长把激烈的情感寄予平静的文字里,让作品在瞬间激发出巨大的能量。正如授奖声明中所表达的,特兰斯特勒默的作品“以凝练而清晰透彻的文字意象给我们提供了洞悉现实的新途径”,充满了“简练、细腻,充满深刻的隐喻”。
非常巧的是,这位新的诺奖得主和2010年的诺奖得主略萨一样,也多次来到中国,他的获奖也曾被中国人预见,他的诗集也已被翻译成中文出版——1990年,漓江出版社出版了由李笠翻译的特兰斯特勒默诗歌选集《绿树与天空》;2001年,南海出版公司出版了李笠翻译的《特兰斯特勒默诗全集》,大规模地将诗人的10余部诗集全部译介过来。据说他的诗集曾是诗歌发烧友的最爱,现在已然脱销。
特兰斯特勒默的诗风也影响到中国作家的写作。这其实并不奇怪,因为只要认真读一读他的诗行,很明显地可以感受到和中国古诗一样的亲近,有很强的画面感,勾画日常生活和自然时凝练而通透,不同之处只在于,他的诗歌意味更深远,内在的逻辑更充分。
对于诺贝尔文学奖,一直有诸多的争议,大家最津津乐道的是托尔斯泰、马克·吐温和易卜生等许多作家都与该奖擦肩而过,而一些我们并不熟悉的诗人、作家却榜上有名,尤其是评委们近些年更多关注一些描写权力下个人命运的作品,引发大家对于评选“政治化”的批评。但不得不说,在诺贝尔文学奖百年的获奖名单中,泰戈尔、叶芝、福克纳、艾略特、马尔克斯等大多数人还都是当之无愧的。
对于中国作家何时获奖一直是媒体所关注的。诺贝尔文学奖评委曾经表示,中国一些优秀的作家还没有获奖是因为语言的翻译问题。这也许是实情,也许是托辞,但翻译显然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之所以能在全球范围内经久不衰,应该归功于格雷戈里拉贝撒的出色翻译,该小说在获奖之前已经被翻译成几十种语言。土耳其的帕慕克也非常幸运,他最著名的著作《我的名字叫红》的英语和其他欧洲语言的翻译质量都非常高,译者埃尔德格高克纳以行云流水的英文再现了帕氏缜密的句子,为其作品再翻译成其他文字提供了非常好的样本。据说日本在向世界推荐川端康成的作品时,专门将翻译者请到日本来熟悉日本文化、学习日本民俗,对于川端康成作品中那些展现日本唯美风情的书法、茶艺、能剧等都进行了专题性的解读,以便让翻译者明白其精神价值。这也是川端康成的作品能够被世界接受的原因之一。如果说德语、西班牙语、法语属于国际通用语,那么日语、土耳其语显然并不是,我们也许需要利用广泛的国际合作来传达中国文学的精髓。
据说诗人住在波罗的海的一个小岛上。他并不是一个多产的作家,四到五年才出一本诗集,每本诗集一般不超过二十首诗,写得最久的一首长诗曾耗时整整十年,所以迄今为止只发表了200多首诗。“写诗时,我感觉自己是一件幸运或受难的乐器,不是我在找诗,而是诗在找我,逼我展现它。”看来,没有一个作家会为了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而去写作,选择写作,仅仅是因为那是一种生活方式。
来源:《光明日报》(2011年10月11日14版)
(责任编辑:冷得像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