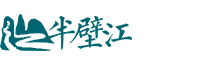|
在此我将试图从一个角度对普世伦理中的普遍底线主义主张做一种更为直接的批评性分析。将伦理或道德领域中的普遍主义和底线主义结合在一起,有其特别的意味。这等于说,在深度伦理的层次上不必追求普遍性,而只在底线伦理的层次上追求普遍性——很明显,这也正是普世伦理的自觉追求。于是就涉及到对于底线伦理与深度伦理的区分——这也正是我要说的那个角度。[17]实际上,对于底线伦理和深度伦理,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区分方式。一种是在一个实际存在的伦理体系内部根据其对生活意义的整体理解划分哪些属于底线伦理,哪些属于深度伦理,另一种则是根据一个外部的参照系——来自另外的某种伦理立场,因而并不内在于任何一种实际存在的伦理体系——来确定哪些属于底线伦理,哪些属于深度伦理。这种不同的区分方式意味着,对于不同伦理体系的践行者(agent)而言,不仅在深度伦理的层次上存在分歧,无法公度,而且在何谓人类伦理生活的底线的问题上也存在分歧,无法公度。举例来说,对于一个基要主义的基督教信徒来说,信仰十字架上的基督就是一个最低限度的伦理,不信当然远比一些一般意义上的道德罪恶(甚至是一些严重的道德罪恶,比如谋杀)更为严重。但是,“信仰十字架上的基督”当然不可能成为一种跨宗教、跨文明的底线伦理。如果考虑到任何一种宗教与信仰的关联,那么,这个例子就很能说明问题:任何一种宗教性的伦理体系内部所确立的底线恰恰是普世伦理所要寻求的底线的反面,也就是说,在宗教性的伦理体系内部所确立的底线,恰恰属于普世伦理中所区分出来的深度伦理。揭示出这一点对于我们理解普世伦理的困难很有助益。不过,由于这个例子直接涉及到信仰问题,所以可能有人会提出异议说,正是因为混淆了信仰与伦理,才导致上述的推论。尽管对于一个信徒来说,其伦理是通过其信仰建构起来的所以只能在信仰的语境中才能得到理解,但是,信仰与伦理仍然是两个不同层次的问题,而且普世伦理恰恰就是要将信仰的问题与伦理的问题区分开来。只要恰当地区分信仰和伦理,将问题限制在伦理层面,而不是信仰层面,就不会有上述推论。与此相关,做人的底线(主要涉及到“我是谁”的问题)与伦理的底线(主要涉及到“我如何与他人共处”)就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如果说对于一个信徒来说信仰指向其人格认同因而具有建构其整个人格的力量,那么,伦理则是一个更为特殊的领域,比如说可能指向自我与他者之关系的建构。把做人的底线等同于伦理的底线同样意味着混淆。 这两个有针对性的且相互关联的反驳看起来有效,而且也有助于我们对普世伦理的进一步理解,但从根本上来说并不解决问题,因为我们仍然可以就伦理的层面找到更有说服力的例子。比如说,一个儒家精神的服膺者会将“孝敬父母”作为人之为人的伦理底线,但这一点却不一定能够成为——至少目前还没有成为——一个跨宗教、跨文明的底线伦理。[18]“孝敬父母”说的是伦理层面的子女与父母的关系问题,不是信仰层面的人与神的关系问题,但是同样在普世伦理的建构中可能被归为深度伦理而在某种实际存在的伦理体系——儒家伦理体系——中则被归为底线伦理。另外,在儒家伦理体系中,“孝敬父母”既可以被理解为是做人的底线,也可以被理解为是伦理的底线。实际上,黑格尔早已深刻地揭示出,人格的建立一方面在于自我的认同,另一方面也有赖于他者不可或缺的承认。也就是说,在人类生活中总是存在着一些有意义的、重要的他者,对于我们的人生与人格认同具有建构作用。因此,在做人的底线和伦理的底线之间,本来并没有清晰的界限。 这就意味着,不同伦理体系中的人们不仅在深度伦理层面存在着不同的、乃至无法公度的观念,而且在底线伦理的层面也存在着不同的、乃至无法公度的观念。究其原因,则在于任何一种实际存在的伦理体系都包含自身对于底线伦理与深度伦理的划分,因此,要接受或容纳一个外部参照系所划分的底线伦理与深度伦理——显然不可能与内部划分相同——就需要对其正当性进行合理性证明。在我看来,普世伦理的普遍底线主义主张的真正要点和难点,首先就在这里。将伦理领域的无公度性理念贯彻到底,也就是就此宣布处于任何一种实际存在的伦理体系中的人——如果是一个忠实的、持内在立场的践行者的话——就没有正当的理由接受或容纳对底线伦理与深度伦理的外部划分。这就无可避免地退回到了彻底的相对主义立场:在不同的宗教与文明之间无法达成真正的伦理共识,无论是深度的还是底线的伦理。那么,这是不是一个合适的推论呢?实际上,这里所做的是一种静态的分析,虽然在许多时候有其现实意义,而且在理论上也有其深刻之处,但却忽略了人类伦理生活的动态机制和完善能力。前文已经提到,普世伦理的达成,是经由宗教对话与文明对话,而通过建构一种哲学人类学或许可以为一种普遍底线主义的普世伦理提供合理性证明,但被普世伦理的倡导者出于某种合理的理由而拒斥。[19]而对话恰能体现出人类伦理生活的动态机制和完善能力。实际上,只有将我们的目光聚焦于对话这个具体的领域,才能真正理解普世伦理的可能性及其意义。 对话首先必须具备必要性。普世伦理的倡导者们常常将之泛泛地刻画为为了避免宗教或文明之间的可能冲突及其带来的人类苦难,这当然不错,不过,在此我想强调的是对话各方的内在必要性,或者说是伯纳德·威廉姆斯意义上的“内在理由”,亦即,必须是对话各方从自己的内在立场出发认为对话是必要的。对此,我们可以做出如下简要陈述。首先,既然宗教多元、文明多元是一个客观事实,那么,任何一种宗教或文明的践行者都要面临如何处理与跨宗教、跨文明的他者的关系问题,而与他者的对话正是处理这个问题的一种积极的努力;其次,既然他者的不同视野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促进自我反思,加深自我理解,那么,对话对于自我的存在和完善的重要性就是不言而喻的;再次,如果一种宗教或文明的践行者完全出于自身的宗教或文明信念认为自己所处的那种宗教或文明承担着或应该承担全球性的普遍责任,那么,倡导宗教对话或文明对话对这些践行者而言就构成了内在理由。[20] 对话还必须具备一定的伦理条件才能被对话的各方所接受,比如说圆桌会议模式,否则会导致拒绝对话的局面。这里最重要的理念当然是平等与宽容,以及相应的程序性理念——比如民主。这里值得指出的是,如果将对话的伦理条件等同于企图通过对话所要建构的普世伦理,实际上是降低乃至取消了对话的意义。基于平等与宽容理念的对话不需要通过对话再谈出平等与宽容的伦理理念来。那些旨在保证平等对话的程序性理念一样也是对话的基础或前提而不是对话的目的。[21]不过,对话的伦理条件仍然构成普世伦理的一部分,因为这是其可能性的保证。 至于对话能够达成什么样的共识,可能是许多人考察普世伦理问题时最为关心的了。不过,根据前面对对话的内在理由的分析,我们能够推知,达成共识其实并不是对话最重要的目的,因为即使达不成共识,对话仍然有其内在的意义。一个务实的做法是考察何种意义上的共识既可避免太大的难度又能在文明多元的世界中起到恰当的作用。这就涉及到普世伦理中的底线主义诉求。对此,迈克·沃泽尔在《厚与薄》一开篇的设例极具启发性。他说,当一个遥远的旁观者——不管是谁——在电视画面上看到布拉格的游行队伍高举着“真理”与“正义”的标语,尽管可能对于游行者想要捍卫的“真理”和想要伸张的“正义”缺乏任何具体的了解,但是,那些标语仍然有意义,也就是说,旁观者仍然能够加入进来和他们一道游行。在他看来,这是因为诸如“真理”、“正义”这样的词语不仅既有其形式意义,又有其实质意义,而且在实质意义上既有其浅层意义,又有其深层意义。一个遥远地方的旁观者虽然无法理解其深层意义,但可理解其形式意义和浅层意义,这构成相互理解的跨语际基础,因而也是底线主义得以运作的恰当层面。[22]于是他认为,底线伦理着意于提供“一个批判的视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并不需要将其所倡导的伦理观念具体化,反而就是要保持其抽象主义面目。[23] 也就是说,由此建构起来的底线伦理并不是实质性的或建构性的伦理,而只能是调节性的或范导性的伦理,它服务于人类交往的一个非常浅的层次,甚至仅仅是一个理论模型,可以嵌入任何一种实际存在的伦理体系,但是只在某些特殊的事务——也就是人类交往的那个非常浅的层次上发生的一些事务——上发挥作用。[24]至于人类交往层次的深与浅,可以从伦理所对应的实际生活领域去理解。就像家庭伦理对应于家庭,社会伦理对应于社会一样,普世伦理对应于世界——只不过这是一个抽象出来的世界,既不虚假,但也不够真实。这样一个抽象出来的世界[25]又比较符合人类目前的实际情况:目前的这个世界虽然还不是一个深厚的共同体(thickcommunity),但毕竟已经是一个共同体,可以说是一个比民族国家更依赖于想象的、更加淡薄的共同体(thincommunity)。[26]在我看来,这可能就是直面人类宗教与文明的多样性事实而对底线主义的普世伦理的最合理的预期。[27]超出这个界限就会对普世伦理产生误解,就会导致对普世伦理的理论敲诈。 万师俊人先生大作《寻求普世伦理》再版之际,嘱我作序,兹就我对这个问题的理解奉上,一并请益于师友学人。 本文已发表于《文景》2008年第9期。 [1]比如翟振明:《为何全球伦理不是普遍伦理?》,载《世界哲学》,2003年第3期;赵敦华:《关于普遍伦理的可能性条件的元伦理学考察》,载《北京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 [2]在中文学术界,“普世伦理”的提法来自万俊人:《寻求普世伦理》,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 [3]HansKüng,GlobalResponsibility:InSearchofaNewWorldEthic,SCMPress,1991. [4]有关这次会议的情况可参见孔汉思、库舍尔编《全球伦理——世界宗教议会宣言》,何光沪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5]参见《全球伦理——世界宗教议会宣言》,第88-89页。 [6]强大与阔达往往紧密相连。另一种来自基督教的阔达立场是查尔斯·泰勒在《天主教的现代性?》与《今日宗教之多样性》等书中表达出来的。泰勒同样认可文化多元主义,同时对基督教文明以一统多的普世理想有强烈信念。参见CharlesTaylor,ACatholicModernity?:CharlesTaylor’sMarianistAwardLecture,withresponsesbyWilliamM.Shea,RosemaryLulingHaughton,GeorgeMarsdon,andJeanBethkeElshtain,OxfordUniversityPress,1999.请注意“Catholic”一词有“普世”之义。以及CharlesTaylor,VarietiesofReligionToday:WilliamJamesRevisited,HarvardUniversityPress,2003. [7]比如何怀宏:《底线伦理》,辽宁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8]虽然很快还发生了“科学与人生观”的争论,但人生观问题很长时间并不受重视,因为不是当务之急。由此也可以思考现代新儒家在中国现代史上的意义,他们始终关注的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最为看重的“伦理觉悟”的问题,尽管立场与“五四”的主流倾向完全相反。1949年以后的人生观问题只能在共产主义的思想框架内被理解,表现为共产主义理想对中国人心灵的塑造,即“为共产主义理想奋斗终生”。 [9]这并不必然否定自由主义,恰恰相反,自由主义一直就是针对这个问题的一种“理顺”方式。关键在于,自由主义能够真正成为一种理顺二者的方式,需要一定的条件,那种无条件的自由主义主张其实是一种天真的政治浪漫主义。 [10]这可以说是华人学者的一个共同倾向。华人学术界倡导和推动文明对话的最力者当数杜维明。关于万俊人的普世伦理构想和孔汉思的全球伦理构想的比较,可参见王晓朝:《论全球伦理与普世伦理的理论构成及其出路》,载傅有德主编:《跨宗教对话:中国与西方》,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版。不过,本文对二者之差异的理解与王晓朝的理解有很大不同。 [11]认儒家为宗教并彻底站在儒家立场上深入考察全球伦理的重要著作是刘述先的《全球伦理与宗教对话》,河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该书初版,也是繁体字版,是台湾立绪文化公司2001年版,与《寻求普世伦理》的初版时间在同一年。需要说明的一点是,本文讨论的主题是普世伦理的中国语境,其中的“中国”当然有其政治意义,但首先是个文化概念。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这个主题应当将更为广泛的华人社会乃至学术界所谓的儒家文化圈都包括进来。实际上,《寻求普世伦理》正是万俊人应新加坡东西文化发展中心之约所撰写的一部专著。不过本文的讨论主要涉及中国大陆学术界。 [12]这一主题与“中国问题”的相关性是不言而喻的。 [13]麦金太尔在《追寻美德》一书中对这一点做了非常精彩的刻画和分析,参见宋继杰中译本,译林出版社2003年版。 [14]或许这就是后现代的伦理状况。从建构全球伦理的方法论来看,孔汉思显然对此有明确的洞察,但他所关注的仍主要集中在宗教与伦理的关系问题上。 [15]张祥龙:《全球伦理如何体现家庭与孝道的根本地位?》,载《基督教文化学刊》第6辑,宗教文化出版社2001年版。 [16]这并不是哲学伦理学的主题,而是知识社会学的主题,参见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黎鸣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 [17]在英文学术界,这种区分被刻画为“minimalismandmaximalism”(可译为底线主义和充量主义),或“thickandthin”(可译为厚与薄)。在中文中,我将使用“底线伦理与深度伦理”来表达之。参见MichaelWalzer,ThickandThin:MoralArgumentatHomeandAbroad,UniversityofNotreDamePress,1994.该书第一章“道德底线主义”(MoralMinimalism)中译文已由唐文明译出,载万俊人主编《20世纪西方伦理学经典》(IV)第286-299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18]比如在西方现代性文化中,子女对待父母的底线伦理可能是履行赡养父母的义务而不是孝敬父母。张祥龙在《全球伦理如何体现家庭与孝道的根本地位?》一文中,正是要站在儒家立场上就这个问题来重新探讨全球伦理。 [19]需要补充的一点是,以哲学人类学为基础建构普遍底线主义的普世伦理其实也正是道德形而上学的思路。也就是说,道德形而上学所留意的,恰恰是人类生活的底线伦理,而不是人类生活的深度伦理,比如康德在其《道德形而上学基础》中所举的恰恰是“不许撒谎”、“不许杀人”等一般被认为是底线伦理的例子。 [20]实际上,孔汉思以“全球责任”论“全球伦理”,正可作如是解。因此,值得我们中国人思考的一个问题首先是:中国文明是否应该、是否能够、又如何能够承担全球性的普遍责任? [21]在《厚与薄》一书中,迈克·沃泽尔批评了哈贝玛斯的程序普遍主义。参见MichaelWalzer,ThickandThin:MoralArgumentatHomeandAbroad,UniversityofNotreDamePress,1994.p.11. [22]这里加入了我的理解和概括,参见MichaelWalzer,ThickandThin:MoralArgumentatHomeandAbroad,UniversityofNotreDamePress,1994.Chapter1. [23]沃泽尔将“抽象艺术”(MinimalArt)与“道德底线主义”(MoralMinimalism)加以类比,注意到二者的相似性。英文的“MinimalArt”恰恰被正确地译为“抽象艺术”,也表现出“底线”与“抽象”的联系。参见MichaelWalzer,ThickandThin:MoralArgumentatHomeandAbroad,UniversityofNotreDamePress,1994.p.7. [24]就前面提到的中国问题来说,这一点告诫我们,切不可将普世伦理问题混同于中国问题,也就是说,建构一种普世伦理并不能代替中国问题的解决,反而是,中国问题的解决能够为普世伦理的建构提供一种保证。 [25]可直接称为“抽象世界”。学界曾有关于“抽象社会”的专门讨论,但还没有关于这里所说的“抽象世界”的讨论。 [26]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吴叡人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版)一书中指出,民族国家作为一个共同体建构于想象,其客观条件是印刷术等大众媒体的发展。世界作为一个共同体当然更是依赖于以大众媒体的发展为客观条件的想象活动。请注意在沃泽尔的设例中电视的重要性,他也明确提到,这一设例来自他自己的实际经验。 [27]西方文化中对对话的另一个经典理解是所谓的辩谈或辩证法,由此可能导致一个以辩证法为基础的黑格尔式的世界历史观念——这个观念已经饱受批评,本文不做讨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