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写下这个题目,源于极度的震惊。 将爱深植于脑核 这本书,机场候机时,邻座将它扔下。它愚蠢又恶俗的包装,使得我几乎不会买它,但白送就是另一回事了。哪怕出于一种敬惜字纸呢,不轻易放弃任何一本书,就象守财奴不放过一个桐子儿,检起翻了翻。 接下来,整个晚上,我都在为这本书的资料与观点经历一场过山车般的震撼。 我很早就知道,每一个婴儿对母亲的爱是天然的。但不是每个母亲都天然爱孩子。最近得到了关于南京饿死女童的母亲乐燕的消息,她已经产下一个孩子,本来她应该享有哺乳的权利,她却拒绝给孩子哺乳——等于又一次地抛弃了这个孩子,于是被很快收监执行,孩子另外作了安置。这和她以前自己憧憬地说:“要好好照顾这个孩子”的说法完全相悖,却和她当初虐待并饿死这个孩子的两个姐姐的行为模式完全一致。 很多人可能不能理解一个母亲何以如此丧心病狂。在看过了以下这个猴子实验后,也许会明白。 20世纪50年代,(注明时间是因为笔者我极度不赞成这样的实验),哈洛在威斯康星大学作灵长类动物的实验。 一组新出生的小猴被第一时间带离了它们的母亲,独自关押。哈洛给了它们最好的营养奶粉和添加剂,所以这些猴子都长的很壮。但后果是灾难的,所有这些猴子都有自闭与孤独症。它们在金属笼子里滚来滚去,把自己大拇指吮吸到出血。看到其他猴子就害怕得尖叫,感觉到受威胁时,就会表现各种暴力攻击行为,多数暴力行为针对自己,把自己扯得血肉模糊、甚至咬掉自己的手掌。 科学家曾经在一部分小猴笼子里铺了一层柔软的布。没有接触过母亲的小猴很快迷恋上了这些布,它们用布把自己裹起来,如果有人靠近,它们会紧紧挨着布,这是它们唯一的安慰。 而哈洛在另一个实验中,给一些小猴“两个妈妈”:一个是铁丝作的妈妈,一个是毛绒作的妈妈。他把食物都放在铁丝作的“妈妈”手里,目的是想知道,“食物和慈爱”,小猴更想要哪个妈妈?答案是:小猴感到饥饿时会跑向冰冷的铁丝妈妈,迅速喝饱,然后立即回到毛绒妈妈身边,6个月中,每天超过18个小时和毛绒妈妈腻在一起。 哈洛写到:“这些小动物脑子里似乎装着某种程序,天生就要寻找爱。——如果猴子教会了我们什么,那就是在你学会如何生活之前,你要学会如何去爱。” 更糟糕的实验在后头:哈落将一组小猴放在没有任何妈妈的笼子里。连铁丝妈妈都没有。被隔离的小猴像是得了灵长类的精神病,对所有情绪的表达都麻木不仁。它们甚至对自己的孩子也很恶毒,一只疯猴咬掉了自己孩子的几根手指,另外一只看到自己的孩子在哭泣,就把孩子的脑袋塞进嘴里嚼得粉碎。多数发疯的猴子母亲只是把它们所受到的残忍对待又施加到它们的孩子身上。当它们的孩子试图拥抱它们,它们会把孩子推开。茫然的孩子一次又一次地尝试,但都无济于事,它们的母亲什么感觉都没有。 看到这个案例,我等于看到了乐燕。20多年前她被非婚生子的母亲抛弃,她的母亲因为是农村户口,不被夫家接纳。她的母亲在她1岁左右将她扔给了父亲家。爷爷奶奶勉强接纳了她,但也仅仅是“让她活着”。她经常被单独关在家中,坐在防盗门后“野兽一样嚎叫”。因为没有户口,她也没有机会上学。没有母亲、没有社交、没有同伴,在21世纪的南京,她是80后的文盲。和她一起坐台的小姐说:“她自私小气还霸道。”她的邻居亲戚说:“她暴力而富有攻击性。” 人类脑干深处,有一处情绪脑。所有情绪的反馈,发源于此。而理性和理智,是人类思维的最外围阶段。人类真正行为的抉择,是由脑干深处的情绪本能反射作出。 最杰出的棋手不是靠棋谱来下棋的,而是倚靠直觉。就像打高尔夫球的选手,如果他开始在思想里肢解自己的动作,企图让它按部就班地规范——基本上他就输了。直觉必须行云流水一样涌出。又好象作家或诗人的写作,记得写作规律的写作是作文而不是文章,记得语法规律不是诗歌是口号。 回到爱本身,我们能够去爱,并不是我们记得《圣经》告诉我们要去爱,也不是小学生行为手册的规定。而是一种发乎内心的本能。 而这样的本能,是深植于我们的脑干深处的。小猕猴从一出生就寻找爱。一个精神健康的猴子,在孩子死去很多天后,还会紧紧地搂抱着它。小狗也会守卫着公路上被撞死的同伴,哀哭不肯离去。 除非被剥夺了爱的内核,否则,人类的情感本能就是要爱、不顾一切地爱,甚至宁可自己作出牺牲,为爱付出代价。 我很早就发现,人类之所以会行善,是因为行善得到了某种心理的奖励机制。佛教认为布施的对象是自己的恩主,因为他们帮助了自己的修行。基督教也认为“施比受有福”。而在《how we decide》中,一个实验也证明了这样的假想。 一个脑成像实验中,实验者给每个人128美元现金,他们自行选择把钱留下还是捐出。当这些人选择捐钱时,大脑奖赏中心被激活,多巴胺分泌增多,他们体验到了无私的快乐。事实上,有几个测试者在选择捐钱时,其大脑的奖赏中心的活跃程度比他们收到现金时还强烈。在人类的大脑看来,付出比得到好。 而同样,灵长类动物对同类的痛苦有强烈的感知。 6只猕猴,被实验人员教会通过推动2个开关来取得食物,1个开关推开后可以获得大量美味的食物,1个则是只有少量的不好吃的食物。很快,猴子们都学会了推动开关。但有一天,它们推动那个掉下大量好食物的开关时,另外一只笼子里的一只猴子受到了电击,它们听到了可怕的尖叫,也看到了那只猴子害怕得抽搐颤抖。它们立即改变了自己的行为:有4只不再推动那个可以带来最大奖赏的开关,只要不伤害到别的猴子。另外的2只,1只整整5天不推动任何开关,第6只则整整12天不推动任何开关。 那么人类为了爱,为了利他,最高可以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佛教中有割肉饲鹰的说法,而在基督教中,我们可以看到,耶稣为了救赎的信念,可以忍受酷刑、被钉上十字架,并为钉死他的人祷告。 休谟与亚当。斯密都有一个关于“道德情绪”的假想。亚当。斯密说:“因为我们不能直接体验别人的感受,所以我们不知道自己的行为会对别人造成什么影响,只能通过想象自己处于同样情形下是何感受。”这形成了我们的道德基础,中国的俗话是:“将心比心。”或曰:“老吾老及人之老,幼吾幼及人之幼。” 其实,按照现代心理学的理论,它叫做“同理心”,或是人类的情感投射。一个母亲很容易同情一个拐卖的婴儿,而一个找不着老婆的则吊丝很仇视拜金女而同情被拜金女抛弃的伴侣。人们本能地同情弱者,好比一个死刑犯,最初看到他杀人恶行时人人痛恨,但在押送他上绞架时又不免唏嘘。 张鸣教授在他的民国评论中写到:“清兵纵使配备了枪械,但毫无战斗章法,他们大多是对着前方阵地拼命放空枪,不考虑是否命中目标,子弹打完了就溃退。”这种情况持续到北洋军阀时代。 当时我一直认为这是一种怯懦的国民性。 昨夜却读到如下史料:“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准将s.l.a马歇尔访问了上千名刚刚参加战斗的美军士兵:只有不到20%的士兵真的朝敌人开过枪,即使受到攻击。” “人们害怕的是杀戮,而不是被杀。这是战斗会失败的常见原因。”——写到这里,我们也许会对在南京大屠杀中成千成千被牵去屠杀而没有反抗的青壮年有更深的理解。 这些研究成果发表后,美国陆军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调整培训方案,反复训练士兵的脱敏反应——直到杀戮成为一种自动反应。跳开一步说,知道了这样的政策,我们也许不再对维基解密中曝光的“美军用瞄准镜远距离恣意射杀一群平民”(目前我们看到的孤立事件)的惊悚视频感到意外。同时,军队开始强调战场技术,使用如高空轰炸、远程大炮等战术,为了降低战争的人际性:人们不用面对随后的死亡。 写到这里,我忍不住又要荡开一笔。 直面杀戮时,日人有一种天生残酷的种族天赋。之所以是种族天赋,是因为它由来已久。南京大屠杀已众所周知,众所不知,早在日俄战争中,日军占领旅顺港,有组织地对全旅顺平民施加虐杀,方式手法,与南京大屠杀一辙。以一个客栈现场为例,客栈中所有人都被杀死,从被杀死在母亲身边的儿童、和母亲紧紧抱在怀中的吃奶婴儿,到倒在马厩中被奸杀的年轻使女。而与此同时,东京的公园中,为了庆祝这次战胜,许多人挂起一个特别制作的灯笼庆祝游行,灯笼糊成一个被割下的支那人的首级。也许以血腥残杀为勇以自残为尚的文化基因使得他们已经天然脱敏,逾越了“战争的人际性”?轻易把杀戮变成审美和娱乐?德国人在二战中也干了许多灭族之事,但他们为了遮掩或回避直接面对,制造了“集中营”,用白手套来干这些直面杀戮的事。当然,如果读过《檀香刑》或《刑罚的历史》,又或《酷刑史》、《黑白二十四史》等,会非常羞愧地发现,要论虐杀与酷刑的资深,中华本族在自相残杀时的凶悍,强者凌辱弱者、弱者凌辱更弱者时,也可以在文明史上独树一帜。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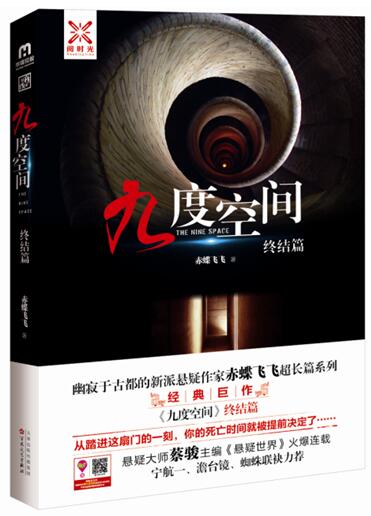
 京公网安备11010202007521号
京公网安备11010202007521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