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德勒兹说你看它是零零碎碎的“小”寓言故事,minor不是小孩的意思,是次要的意思、是边缘的东西,但是,你看卡夫卡的小说里写的那些东西,《地洞》里面那人像个冰冷的耗子似的觉得自己不安全,在这儿留一个出口,在那儿留一个出口。《变形记》里公司小职员早晨起来发现自己变成了大甲虫,甲虫有个特点,它翻过去就翻不回来了,陷入焦虑里边,吃饭的时候他就想下去看看亲戚看到我变成虫子会吓成什么样,人和虫子已经分不开了。这个东西你跟《傲慢与偏见》、跟狄更斯、跟巴尔扎克、托尔斯泰这样的主流文学比较,他没有写出历史,没有写出革命,没有写出现代性,看上去很小,但是,他写出了和整个现代社会的关系,我们简单概括就是“异化”这个问题,是人和整个现代世界在存在意义上的关系和政治意义上的关系,集体的关系。在这个意义上,卡夫卡的小文学就比主流文学更大,因为他没有天真到认为文学就是纯私人的东西,也没有认为文学是个纯自律的东西,不认为文学是资产阶级在打理完个人事务之余也想有娱乐、审美、有他们的梦、他们的性的问题、不能跟人交流但可以写出来无伤大雅的游戏性的事物。这样的一些主流文学的基本前提跟卡夫卡的写作比起来又小了,不够大,它没有触及到绝望、人类的命运、异化、语言内部的陌生感流放感,这些现代性最深层的问题在现代主流文学里的体现往往不如在边缘次要的文学里更充分。 我们看鲁迅的写作,比如《阿Q正传》,不是长篇小说,你怎么把它往上拔也拔不到史诗的高度——是个滑稽故事,流浪汉体,报刊连载;是一个没有情节、没有任何意义上的复杂和不充分的东西;“正传”就是传记,一个传记有它自己的内部矛盾,开篇也有个交待:我这个“传”没有办法“作”,“本记”、“世家”、“列传”之类的“体”,可是它都不合,只好生造两个字来,不是“立言”,就随便抓出两个字来,就是“言归正传”或《书法正传》里抓出来的,说“顾不得了”。整个的故事就是东洋的漆棒、小D的事、秀才娘子绣花床、吴妈的事、不许姓赵的事、不许革命的事……这么一个完全没有充分展开的文本。八〇年代的文学焦虑很大程度上就是看了阿Q以后大家都很绝望,说我们为什么没有史诗,为什么没有长篇小说,凭这种东西怎么能拿到诺贝尔奖。但是《阿Q正传》从语言、形式、叙事和寓言的层面上来讲,某种意义上是中国文学最大的作品,因为阿Q就是中国,不是隐喻上的,阿Q就是中国,就是“中国的传”,是对中国人集体传记在语言和叙事形式上的不可能性和可能性的寓言性探索。以前我们说里面有民族性,落后性,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其实还可以读出别的东西来,这就使整个中国文化作为“命名系统”的“不可能性”、“传”的“不可能性”被《阿Q正传》写出来了,从而把意义的命名行为、价值和“难堪状”在各个层面上给“再现”出来了,representation就是allegory。这要比电视剧式的叙事更具有文学性,像《闯关东》、《金婚》这样的情节剧,一写几十年,好多故事,反而小了。这样的作品再怎么“大”也不如《阿Q正传》大,因为《阿Q正传》不是写实的小说,也不是现实主义的小说,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章回小说,什么“体”都套不进,不符合,完全是个边缘的、“次要的”、讽刺性的东西,但它却具备一种文学写作的张力和寓意能力,具有一种语言内部的激进性和艺术体制内部的颠覆性。这种内在的张力同作品外部环境形成一种对应或呼应关系,由此而确定了《阿Q正传》的伟大意义。 德勒兹最后亮出了自己在文学性问题上的立场:真正的文学是要能通过语言的实践和行动不断地保持、恢复、重新激发文学写作语言内在的激进性、革命性。革命是在这个意义上的,审美形式上的,只有在小文学里,只有向语言和写作可能的边界不断冲击,这样才能不断地让文学把自己建立起来。换句话说就是,文学要“小”就不能“大”,文学要“大”就必须“小”。这是德勒兹的结论,这是个非常反中产阶级主流、文学体制、文学消费、文学审美的力量。越读鲁迅就越觉得是这样。在客观的意义上说,当代中国批评是接受这一点的,但在意识的层面上不接受,我们在自身传统中接受了,但在今天的写作、论述、媒体和学术语言中还不接受。觉得返回30年代很老套,但中国文学研究界又反反复复离不开鲁迅,不断去读、去想。鲁迅的全集现在是18本[200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版],它是个大文学还是小文学?它是个大文学,这在更大的传统中实际上是被接受下来了。但重读鲁迅对当前关于纯文学的讨论、文学形态的讨论、20世纪中国文学的讨论都会非常有帮助。这一点我希望能反过来激发对文学批评的讨论。 下面我们谈一下民族寓言(NationalAllegory)的问题。在这里我们不要过多纠缠于为什么西方文学就是文学本身,就高级,而我们偏偏要被戴上个“民族寓言”的比标签才能进入世界文学和文学批评的理论视野。这是不是在贬低我们,说我们没有那么厉害,写不出像西方作家那样的“纯文学”、“真正的”文学作品。如果我们避开这个概念,从正面理解“民族寓言”,我觉得杰姆逊这个概念和德勒兹的大小文学概念非常相似,它指的无非是在一个中产阶级革命和体制化建设没有充分完成的社会,即一个没有充分分化、分层、法制化、私有财产的符号化、法律符码的科层化都没有充分完成的社会,人和人是休戚与共、命运与共,生活在一个共同体里,不管好坏。这就像以前我们住在大杂院里,一家人住一间房,亲戚朋友谁也分不开,你没有隐私,没有一点个性,可是现在我们有隐私了,同时也在哀叹人和人隔这么远,人都没有归属的感觉,没有共同体的感觉。在资产阶级市场和法制没有充分体制化的社会里边,任何一种写作都不可能是资产阶级的私人写作,哪怕你在写私人语言、私人身体,你还是会一不小心写到你的同事、领导或党、政府,因为你的“私”是被这个“公”界定的,或多或少是对这种“公”的指控或反叛。你不可能完全把自己从周围的环境中撇干净。这么看,杰姆逊就等于是在说,非中产阶级写的就不是中产阶级文学。关于这点有很多人抗议,抗议的名目是西方中心论,从意识形态的角度理解就是抗议你们这些已经充分中产阶级化的西方学院、教授不许我们做中产阶级,那等于是阿Q去抗议赵家不许他姓赵一样,为什么我们不能做中产阶级,不能有中产阶级的大文学,为什么我们一定要是小文学,谁说我们非要写出政治性、集体性,谁说我们一定要保持文学内在的张力或者说激进性,谁说我们一定要写出真正意义上的“重大题材”,卡夫卡意义上的重大题材?因为跟卡夫卡题材的重大性相比,一般意义上的现实主义小说的题材还不够重大。中国人在文学问题上对杰姆逊这个民族寓言说法的抗议实际是说,我们为什么要背这个担子,为什么我们不能把文学就当一幅画,就当作安乐椅,艺术就是安乐椅,下了班往那一坐,烤着火,喝着酒,很舒服,何必一定要是国家民族、国难当头搅在一起。杰姆逊不是说一定要把这些搅在一起,而只是说,客观上说,一个人写出纯粹内心的、私人空间的、潜意识、甚至是性这样的问题,总会投射出各种各样的集体、政治、历史的影子,这是个非常直白的观察。他是个在西方教文学的教授,他跟他的西方同事和学生们说,你们拿到一个非西方的作品,非洲的、阿拉伯的、亚洲的,你们首先有个标准就是说,比如写的是不是跟托斯托耶夫斯基差不多,不够这个标准就不看。杰姆逊说你们真亏啊,人家非西方人看得懂,中国人读鲁迅读得津津有味。当然他是个马克思主义者,他同情中国革命,愿意有一种对他人的想象,觉得如果没有办法去参与他人关于自身的历史和集体的命运的想象的话,这进一步印证了中产阶级彼此的孤立,私人空间的局限性,他其实是讲了这么一个东西。遗憾的是在非西方世界里,对杰姆逊理论的接受反而不好,很多人只是认为他是个傲慢的美国文学教授,觉得杰姆逊以为你们只能写出寓言,真正的文学是我们的事。其实恰好说反了。 我刚才已经讲到了鲁迅作品内在的含混性,文体学意义上的含混性,每一篇里面都有这样的含混性,散文诗、杂文、小说、政论、时感、杂感,道德文章,鲁迅最后还是道德文章。另外作为一个小注脚,我想把周作人给拉进来,周作人写《中国新文学的源流》,这个非常有意思,他实际上是通过所谓的文学起源、源流问题,拿文学史写作的方式打了个幌子,提出文学本体论的问题,这点非常狡猾。这实际上是德•曼想做的工作,但好多人做得真是没有周作人漂亮。周作人说我们现在要写历史,但写历史碰到一个问题,凡是汉唐、盛世,文学都非常没意思,用俞平伯的话说都是一堆垃圾,汉赋、唐诗都很没意思。反倒是王纲解纽的乱世,有些人逃到山里去了、庙里去了,有些人作隐士了,那种乱世之音他觉得有意思,有颓废的东西、个性的东西,因为他们不做官了,用不着他们为天下操心了。写文学史如果回头看的话,是有这么个“文武之道一张一弛”的意思,文章里也有文武之道,乱就有治,治就有乱,他划出了一个共振幅似的弯弯曲曲的一个线,隐隐约约的中轴线就是中国文学史,但实际上没有这个东西,没有所谓的“中国文学史”这个东西,你把这个东西写出来,按俞平伯的话说完全就是垃圾。如果做文学史编年,那把材料罗列起来就可以了,但如果做中国文学史,牵涉到对中国文学的理解,它(应该)是一个“共时性”的理解,而不是个“历时性”的理解,而共时性的理解是用历时性的方式去写的。这是很聪明的,他就划了个弧线。中国文学这个“源流”就和长江黄河似的,弯弯曲曲,一会流到治世这边,都很没劲,一会又流到乱世这边,都是有劲的,治世和乱世的文学其实是两个谱系,中国文学是两个谱系,两个谱系间完全是断裂的。从汉到魏晋,汉没意思,魏晋有意思,魏晋到隋唐又没劲,晚唐又有意思。但魏晋到晚唐之间没有关系,它中间隔了一个很大的盛世。而盛世和盛世之间也没有历时性的关系,唐代文学和汉文学之间没有直接的师承关系。你要是说韩愈“文起八代之衰”什么的,但周作人讨厌的正是韩愈,没意思。要把点和点之间的虚线拉实,周作人说这是很没意思的。中国文学实际上是两个谱系,都是断开的,虚线,惟一能把让“中国文学史”这个概念成立的方式是提出“文学是什么”这个问题。这就回到刚才德•曼的那个问题,文学史是个主观的东西,是个“判断”,它里面有两种传统的共振,一直到晚清,一直到民国。周作人是用文学史的方式回答了文学本体论的问题。更不用说他一直在通过自己的文学实践重新建立这个“文”的(边界),周作人的文章“淡”得都没有了,那种素和净,他把文学放到一个再消就真没了的境地。像“奥卡姆剃刀”,剃剃剃到最后几乎真没有了,但那点若有若无的东西恰恰是文学最强的、最核心的,它会反弹回来。他的这个“文”的概念比西方的“文学”literature要灵活、复杂、微妙得多。这不是中国文化本位主义,而是,literature我们可以通过非常实的分析、通过历史的、实证的方式去找到这个体制的来龙去脉,它相对来说非常清楚,而“文”的历史外延是非常微妙的。 以这样的“文”的核心概念来衡量今天的散文,大多数是完全不够格。最差的大概就是余秋雨写的那种文化大散文,这是离文学最远的,是一种做戏的、格式化的宣传科文体。我不认识他,也不是想攻击他,只是作为一个读者谈我的感受。我觉得他的散文特别像中学生优秀作文,他当然在知识和辞藻上拉的架子大一点,但按周作人所谓的文章的标准,他的趣味基本上是个初三或高中的语文课好学生的趣味,他们班上所有同学都可能当作家,只有这个人不可能,因为他的写作在语言和形式的政治层面上没有任何紧张和激进性,同历史和集体境遇没有任何抹擦和冲突,而是一种借用、套用现有文学体制(包括文化消费体制)作一些演绎和发挥,归根结底是一种“投其所好”的应试、应制或应市的东西,这种消费品同真正意义上的写作是没有关系的。(郜元宝:现在余秋雨已经进中学课本了。)我的意思是说,“文”的内在活力在外在化的过程中一定要避免许多简单的、形式化的东西。 第三谈谈竹内好。竹内好近年来在鲁迅研究界影响很大,这是个好事,但如果讲过了的话,又会把鲁迅自身的文学性,里面的复杂性遮掩掉,马上会变成一个竹内好的问题,东亚的现代性啊、抵抗啊等等。我觉得竹内好读鲁迅的读法是个非常好的读法,他体会很深,某种意义上来说,他有一种中国人都未必能感觉到的那种体会。就是那种“东洋的悲哀”,他在这一点上对鲁迅的把握是非常准的。但是如果细读竹内好对鲁迅的论述,可以发现它不是一个分析性的,或者是知识性的、文学史的(方式),而是所谓的一个文人读另一个文人,他最后所有最关键的话,都是些作为文人说的话。也就是说,我不跟你哲学家辩论,也不跟历史学家辩论,甚至不跟文学批评家辩论,我就这么说了。他说的“回心”啊,“转向”啊,“抵抗的双重性”啊,对于“新”和“旧”的辩证法,都讲得非常好。他说鲁迅的“新”和日本的“新”不一样,日本的新是把旧改造为新,是优等生文化,是基于日本的现代化。鲁迅不是要把旧变成新,而是证明了旧就是新。这个讲得是蛮不讲理,但我们一读就觉得它非常对。鲁迅的新,他不须要像日本那样把自己变成一个西方人,而是要比一般意义上的传统的中国人更传统,再以传统的方式原地摇身一变变成了新,变成一种革命性的、悲剧性的东西,在虚无和克服虚无的斗争当中变成新。鲁迅可以说是一个是原地不动的东西,而原地不动的东西怎么成为新?实际上这个“新”是个反用的意思,不是简单的新东西的新。 这样的东西出现的原因,一个是因为竹内好有文人气,还有就是同他与日本浪漫派的瓜葛。日本学者自己不太讲日本浪漫派,因为它基本上是个法西斯外围的组织。它鼓吹日本是个“纯自然”的东西,自然本身就是一种浪漫。这种美学的语言翻译成政治的语言就是天皇制,万世一系的天皇制是自然的现象,所以当它受到威胁时,日本人自然要全体“一亿玉碎”了。日本自然而然要有个天皇,民主、革命等要有一个更高的自然的法,自然的正当性,自然的逻辑。竹内好和日本浪漫派的关系是非常复杂的,竹内好同情中国革命(但这与他和日本浪漫派的瓜葛不矛盾,有相通之处)。一方面,他觉得鲁迅代表中国革命和中国大众,通过大众革命式的方式避免日本式的简单西化,中国在自己的原地、在自己的命运当中成为自己的主人,进入世界史,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中国进入世界史了而日本没有进入。这是竹内好非常有批判性的一个观察。但从另一个角度看,他这种非常激进的、左翼的立场是由一种很保守的、右翼的东西支持的,而两者之间的相通处,一丝联系就是所谓“文人气”。竹内好自己的写作是很不守规矩的,而且是有意为之,经常在关键的地方就摆出一副文人气来,你们学者要长篇大论,但我不跟你们在概念上周旋。 我想通过重读鲁迅反过来可以对文学批评在方法论意义、语言批评意义上促成一些反思,这个反思是沿着文学史的脉络来展开的,但核心是希望通过文学性这个概念来重新尝试(文学史解读方法之外的)文本解读。下面所讲的实际上是换个角度把刚才这些重新组织一遍,即重建文学批评概念对重读鲁迅的意义。带着批评的旨趣、理论的兴趣、哲学的兴趣、政治的兴趣读鲁迅,我们怎么读,这是个更具体的问题。 (第二部分) 现在我们转过来看看一种理论的兴趣对于重读鲁迅能有什么提议。我想我们现在读鲁迅,首先要做一个“知识学上的悬置”。我们上本科的时候曾被北大中文系的教师敲打,说你们这帮狂妄分子整天不务正业,读现代派,搞理论创新,但你们要知道,像鲁迅这样的大作家我们一辈子也研究不完;别说你们,就是我们自己研究一辈子也还有好多事情搞不明白。这意思是说,鲁迅研究是“一如侯门深似海”,在知识上有些东西是不可企及的,不可能望其项背的。我不知道鲁迅现在是不是还像这么块大石头压在学生心上,在知识学的意义上鲁迅是一个没有办法去充分占有和了解的材料整体,我觉得这个错误意识要改掉。我们今天做鲁迅,先要做个全知的假定,当然我们生也有涯,知也有限,但必须假定没有任何关于鲁迅的知识是我们不可能去获得的。以前大部分做中国文学的人不懂外语,也不能出国,所以有关鲁迅的一些日文材料不能掌握,现在很简单,去一趟日本就行了;也用不着以德文不行为借口,大家都知道鲁迅和尼采这个关系很重要,可现在不要说鲁迅的德文材料,就是尼采本身的中译也越来越多,你完全可以把和鲁迅有关的尼采全部读一遍,这不是不可能的。鲁迅同进化论的关系,关于鲁迅传记类的材料肯定是越来越多,通过电子检索(很方便就能获得)。八十年代的时候,大家有种很实在的谦卑,说鲁迅的生活世界那么丰富,住在租界里边,有日本朋友,他的生活很国际化,视野很开阔,而我们(八十年代鲁迅研究界学者)五十年代上的大学,也没出过国,生活很局限,一直在国内校园里教书。而现在对于我们来说,没有鲁迅生活的任何一个方面对于我们来说是种秘密,他的消费形态,看什么电影,喝什么咖啡和茶,抽什么烟,见过什么人,这些传记意义上的、物质文化意义上的、文学史意义上的、比较文学意义上的,我们都可以了解。比如日本的北冈正子就做过,就是把鲁迅所有跟裴多菲的、跟莱蒙托夫的、跟拜伦的都可以理得清清楚楚。学术史的意义、思想史意义上的、比较哲学意义上的都可以达到。包括语言的准备,外语、古文等等。“知识悬置”说的就是我们要有“全知假定”。鲁迅的文本对于我们是不设防的,以前总认为鲁迅的文本对于我们是一个堡垒,攻一辈子也攻不进去的堡垒,但今天我们要假定鲁迅的文本是门窗大开,从里到外可以看得清清楚楚,不管做到做不到,但理论上我们可以做这么个假设,没有知识上到不了的地方。说难听点就是再不能用“不了解”做借口了,因为我们现在理论上是可以做到的,做不到的话是“非不能也,是不为也”。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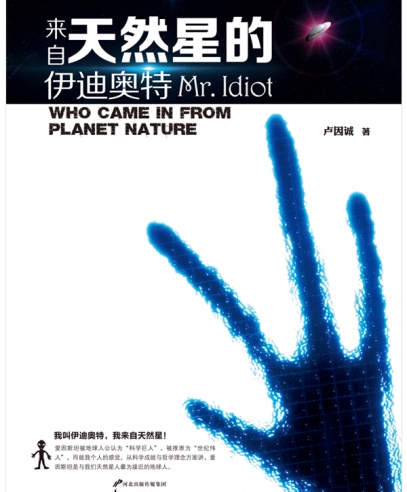
 京公网安备11010202007521号
京公网安备11010202007521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