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孙向晨:其实不止是知识层面上的,比如通过知识储备或者一些挖掘我可以把它消化掉。就是在一些“软”的地方——我不知道该怎么表达——就是在鲁迅独到的一些表达,用这些理论你自己觉得很生硬,或者除开知识背景层面上的这些地方。我表达得不是很准确,大致是这么个意思。 张:“碰到这个问题就暴露了你方法自身的局限性”的意思呢?还是它“具有某种神秘性、完全无法理解”? 孙:就是一些情感、角色上的很难用你现有的这些理论去把握他的,很突兀的一些东西。 张:那肯定有,随时随地会有。但是我觉得这个不是个问题,因为讲到这里,你觉得好像有套路、方法之类的。但实际上我真正读的时候,还是把这些东西都置诸脑后了,还是非常以平常心、一个字一个字地读了,就是比较灵活的。 孙:那么那些突兀的东西,你觉得难以把握的东西是些什么东西?除了刚才讲的那些以外、知识性的层面之外的另外一些东西都是些什么? 张:另外的一些…… 郜元宝:非要把你的一些秘密的东西给“嚼”出来。 张:其实我刚刚更大的一个前提没有讲,我还是回来讲,其实我觉得鲁迅做品里面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神秘性。也就是所有的东西我们都是可以去理解的,我基本上还是这个态度。 孙:也就是平时的话,有没有“疙”到你的地方?那些地方是除了知识性的之外是什么东西?你读文本的时候当读的不顺的时候、很突兀的时候——因为我自己不是这方面的专家,我也…… 张业松:你这个我想起一个问题。旭东这套读下来,通过鲁迅可以重新定义我们现在的“文学性”的东西。然后就是通过你重新定义过的鲁迅和“文学性”之外,鲁迅的作品当中还存不存在另外一些也可以称之为“文学性”的东西? 郜元宝:你的问题是问他这种方法是不是能把它全“吃光”掉…… 张:肯定全“吃光”不了,“全吃光”也没意思了;肯定有许多“剩余物”,这是不言而喻的,也是阅读乐趣所在。这里还是要回到“文学性阅读”的问题来讲。因为对于“文学性阅读”来讲不存在什么被“嗑”一下,因为“嗑”本身就是阅读愉快的一部分,因为在这些关节点上,个别之物和一般的原则通过审美和形式的中介而结合在一起,这种结合往往在认识论和道德领域是不可能完成的。文学阅读里面的“难题”和“不可解”甚至“不可说”的东西正是我们的力量、潜能和自由大显身手的场所,因为讲不通的地方往往也正是“无目的的合目的性”登场的地方。这是跟哲学的阅读和学术的阅读是不一样的,科学式是要“解决”,文学性阅读不是要解决什么问题,任何一个不懂的地方都是最有意思的地方。于是你要想,就迫使你去调整解决的框架、你的预期值——这个不是在科学的意义上,而是以“文人”的意义上。这是一层。第二层关于鲁迅的就是刚才说的重读鲁迅所界定的“文学性”之外的“文学性”,是这个意思吗? 张业松:就是在鲁迅那里还存不存在另外的东西,还有些不可理解的东西、不可全部把握的东西。这种东西我如果在讲如果碰到的话是否称之为文学性?完全无意识的。 张:我想告诉你,我的兴趣刚好就是在碰那些原先认为好像没有碰到的问题,所以我有意识的在找。好像所有的有些疙疙瘩瘩的东西,或者说“嗑”的东西,刚好是我最注意的东西和一些方面。所以如果到目前为止只是做一个交代的话,好像阅读鲁迅还是基本比较“顺”的一个过程。 郜:还有没有没有提问过的同学?——似乎是被张老师强大的理论给“吓坏了” 同学乙:刚才您的一个所谓“寓言式”的解读文本的方法,那么我觉得是不是可以有两种理解的方法——一种是您从像《阿Q》这样的文本中解读除了许多中国近代的文人的思想命运等过程;那么是不是还有另外一种理解,就是说,可能鲁迅的文本只是你个人对于中国近代思想史的一个注解。那么就是说你的所谓完全悬置文学史,或者鲁迅的传记材料,这方面是不是存在着一些缺陷——比如说,是不是可以真正完全“悬置”掉?如果可以“悬置”掉的话,是不是可以避免像我方才所说的从那些方面展开对鲁迅的批评——将文学的材料作为您自己思想的一个注解? 张:我觉得刚好相反,“悬置”的前提是你要知道它,不是你不知道就说要“悬置”。“悬置”的意思是这个意思。群而不论,放在哪里,最后看看有没有一个不期而遇的新的结论,是这个意义上的“悬置”,而不是说“不要了”,也不可能不要。我们读鲁迅也都是在研究鲁迅的脉络里面读,不可能抛弃既定的鲁迅研究的框架来读。不可能离开鲁迅的集体的接受史来阅读鲁迅,这是一个大前提。 至于你说的那个特指的问题,我觉得刚好相反,就是在理论上说,“悬置各种东西”就是要避免将鲁迅作为各种各样解释框架的注脚,或文本的案例。比如说“我对中国近代有这样的看法”,或者“政治哲学”上的、“文化哲学”上的鲁迅就是“那样”——那就是刚好正式要“被悬置”的东西。“文学性”阅读是通过细读文本、打开文本,通过找到作品之间的内在关联——所有的名词、所有的段落、所有的意象、所有的句子间它的复杂的安排,你怎样通过仔细的阅读吧这些安排建立起来。我刚才那个关于阿Q的结论,其实刚才讲得很快啊,好像一步到位一样跳到结论。不信你翻开阿Q的文本,你看看第一段讲什么?速朽的文字。二段讲“名”和“言”的问题,讲“名不正言不顺”、“没有办法写”,之后才是阿Q的故事。就讲到阿Q这人姓什么?不知道。叫什么?不知道?籍贯在哪里?不知道。然后最后说“连形状也很模糊”,然后故事就那么一点点开始了。你说怎么去看阿Q这个人的性格里面的“人性”、“非人性”和“国民性”,或者他的“落后性”什么的,这个反倒是一种先入为主的读法。你说字面的读你能读到这种东西,在这个文学写作的各个层面里面作者非常精心的布置,做的那些“手脚”、用得那些很深的用意,你是这样把它们读出来的。之后我的一个结论是:阿Q是在一个“命名系统”里面无法安放的一个东西,你这样的话是会影响到一个前面的情节。比如说赵太爷不许他姓赵,以前的最直接的读解是“地主阶级对农民阶级的压迫”,可那个就太简单了。实际上合着文章的脉络下来读的这么一个过程,你“顺藤摸瓜”,顺着文章的纹理去读,这样的话,会读出一些意想不到的东西来。 往往我们自命为文学的阅读、最正确的阅读,往往是最先入为主的阅读,因为你脑子里已经有了一堆概念——什么是文学史、什么是鲁迅、什么是启蒙或者什么是“纯文学”,这是一系列先入为主的观点。读鲁迅的时候,你其实是在自己的阐释框架里打转。所谓的悬置就是要悬置这些阐释的框架。当然最后面的一点你说那个阅读的兴趣是从哪里来。当然只能从近代以来中国的社会的、思想的、政治的,从我们今天生活在中国的人的一系列非常具体的问题,共鸣精神问题上,有着这样的所谓的“前理解”(pre-understanding),这是没有办法的、没有人能逃避的问题。但是这里面要通过一系列批评的努力,重新和文本发生关系,重新承认文本的一些自律性,不是在文学体制意义上的自律性去承认它们,而是要顺着文章的纹理,把它最细微的地方读出来。有的时候觉得这个比喻不恰当,但是我觉得读鲁迅就是那么回事,手表匠把手表拆开来摊成一桌子,然后你看是怎么样把它“对”起来。这个工作你说没有理论的话也可以做,我们也不是要用理论“武装到牙”,但是有理论、有方法、知道这些事儿,我觉得要比不知道这些事好。 这样的看法同样也适用于鲁迅研究,看哪些传记、哪些文学史的材料——所有的这些包括他看什么电影、穿什么衣服、家里房子是什么样的、和什么样的女性交往——所有的这些都是相关的,知道比不知道好。但是知道了以后在读作品的时候,当文学作品读。而读文学作品,在座的各位可能都是中文系的,如果各位对“文学”有一个基本的热爱的话,回想我们自己第一次读文学作品就是为了文学而读,很单纯的快感在里面,没有想过这个里面有什么意义、有什么价值,对学术史有什么意义、对思想史有什么意义、在批评方法上可以成功为我“作注”——没有这些问题。这种“直接性”,往往是那种在一定的环境里面摆脱一系列方法的干扰、系统的干扰、体制的干扰的很直接的方法,这个是最直接的和文学的关系,再把这个上升到一个“方法”的高度,这就是文学阅读的方法——不同是一个思想史的材料。我不是把阿Q放在一个既定的近代中国的价值判断里面来读,恰恰相反。 同学丙:我来问一个问题。就刚才你所说的“作者死了”的问题。那个悬置,就是在所谓悬置的视角之下。我们可不可以不说作者死了,而是作品出来之后作者才真正活着了。海德格尔在《艺术作品的本源》里面讲,只有作品创作出来后,才把作者与作品保存下来。在我们的整个研究中,作品是活着的,作者也是活着的。甚至可以讲,作者没有死,作者就那样活了。是不是可以这样讲? 张:对,当然可以这样讲——作者只通过作品活着。但是鲁迅不一样,鲁迅是我们不得不正视的一个人。鲁迅是它所有的作品之上、之下、之外,都有一个非常强大的“先生”凝视着我们,时时刻刻处在“先生”的凝视之下,这个要比鲁迅挂了个藤野先生看着他“不敢偷懒”的力量要大多了。我们时时刻刻处在自己想像的鲁迅的凝视之下。 同学丙:关键就讲一点,就是作者死了和上帝死了还不一样。上帝和我们的关系同作者和作品的关系是不一样的。像我们就要通过鲁迅的作品来了解他、来靠近他,但是上帝和作者是不一样的。用“上帝死了”来理解“作者死了”是不恰当的。用中国传统的文学史来说,我们看到六经里面的“圣人”。“圣人”的形象是通过“君民”来建立起来的…… 张:也不完全是,我明白你的意思。圣人的形象难道不就通过政治权力、历代的…… 同学丙:也不是这个样子。我就说到荀子,我是做荀子的。荀子讲到,孔子论述思想的学习阶段是得其术、得其智、最后得其为人,只有你自己学到那个境界的时候,才真正让那个“文王”“活”起来,就是,让经典活起来了。这个我就想到你刚才讲的中国文学史家搞批评,这个里面是有个传统在的。我们就在这个谱系里面让鲁迅这个任务真正活起来了,真正呈现出来了。 张:问题是,这个文学史和你这个读经不一样。我就要问你,有没有读过古人写的荀子研究史?荀子思想史或者儒家思想史?没有吧。一代又一代的人形成了一个阐释史,但是没有一个人拿着皇帝给的985研究经费去做一部“道德史”,或者说“儒学导论”或“儒学概论”之类的东西。 同学丙:那我就讲这个历史的意识,而不是历史本身。我讲的是历史的意识,这个是传统过来的。但是你说做文学史是不是好、是不是恰当,那个是另外一回事情。就意识本身,是表达了我们对历史的一种感觉、一种领会。我们就是这样领会的——我不知道这样讲了是不是对。 张:我知道你的意思。这个没有不对的地方,可是文学史特殊的地方在于这样:我们如果承认“文学之所以为文学”,第一它要有人读,一个人对文学要形成自己的判断,而这个判断最终是一个好坏的问题,确实有美不美、好不好、作品成功与失败这样的问题。形成的文学阅读活动的持续不断的过程,那么在哪一点上我们可以为文学史做辩护?我找不到任何一个点——凭什么一个文学史家可以插进来,说“我来写一个文学史”——他凭什么这样写?他是基于对于文学本身的判断呢?还是基于对文学价值的判断呢?还是做一个取舍呢?孔子删诗,那么现代的人是不是“选家”呢?——好像又不是。最差的,他只是为了要评职称,他要写一本书,于是他只会写这个,于是他就写了。那么这个跟文学又有什么关系呢?它叫这个“文学史”,包括用“文学史”这个名字这一点,它跟“文学”是什么关系?它跟“史”又是什么关系?我就是这个意思。 至于你要把荀子讲出来,倒挺有意思的。我刚才想了一下,我刚才讲的那套,可能还是有点偏“西化”的感觉。你把荀子抬出来,我们就立刻觉得自己太西化了,本来还以为很“中国气派”的。 郜:不是的,考虑文学史,不是总考虑那些最差的文学史,而是要考虑那些最好的文学史。我们就是通过文学史来做文学批评的。 张:对,是这样的。就是这样的,真正好的文学史就是文学批评,一个时代的文学批评,在一个时代的框架里边。在确定文学的意义和价值上,它实际就是文学批评,最广义的文学批评。比如说我们现在认为,我们现在怎么看待那些老的文学史。像唐弢的文学史是好的文学史那样——不是,他们就是好的文学作品。这个好坏不是我们和他们的“政见”合不合,而是说他们就是能够代表一个时代对文学的基本的判断。你哪怕用了“文以载道”的观点,说那个《毛诗大序》好,那个你可以说是文学史,但它也是文学批评啊。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好”。但是现在的学科意义上的、为生产而生产出来的文学史,我是觉得没有太大的意义。反过来的,里面的一个“量”是我们文学生产“美国化”的一个恶果。它就是“以量取胜”、大量生产,而生产出来以后,你让一个学生展示“中国文学”的书架,如果100多架里面90多架都是“文学史”的,只有一两架的作品、只有那么一格的文学批评,那你说这个时代的所谓的“知识”,你该怎么讲呢? 郜元宝:刚才你讲到那个“奥卡姆剃刀”,我想起我心里面一直(有疑问的)。我不知道以前的学者有没有解决过:鲁迅和周作人“剃”中国思想的时候,他们的方法和效果都差不多;我们现在可以试想一下把他们“打通”。可是他们“剃”了之后,他们各自的文章、各自的“文”的效果就不一样——鲁迅在“剃”别人文章的时候越写越“丰裕”、越写越大,里面的词汇越写越丰富;但是他弟弟呢,越“剃”越“干”,你刚才说的那个“素”、“静”也是一种文学性的表现,但是我不知道撇开这个思想不说,周氏兄弟的文章放在一起的时候,都是两种“文学性”的话,怎么样吧他们调和起来?或者说怎么共存于整个中国文学史上的? 我经常谈到,讲到一个判断就是“我喜欢鲁迅的文章”。我也尊重周作人的学识和修养,但是文章我就没办法喜欢。但是也有人认为周作人的文章很好,还有人还说“周作人是一个字都不能改”,包括郁达夫也这么说“那真的是‘增一字不得、减一字不能’”。我不知道你从你的体会中看,你如何判断周作人的文章,你到底如何看待他?文体本身好在什么地方? 张:周作人的文章,我觉得有一部分很好,有一部分你其实是再怎么看都很难给他“开脱”的,真的味同嚼蜡。尤其后期的“掉书袋”的东西,基本上好的就不多。但是他的好文章,就是20年代到30年代的那些好的文章,那个是真的好。怎么好呢?我觉得有几点:很简单的讲一下,周作人要说起来又是一大堆,但是好的地方简单讲至少有一点,就是他的文章不是你读得有多舒服、有多少快感,他那个——好有点像我们听楼上一个业余钢琴家谈《致爱丽丝》或肖邦《夜曲》什么的,觉得很美,但你楼上住的如果是个职业钢琴家,他弹的东西你可能会觉得一点也不好听,有时简直不是给人听的。文学内部一些最高端的、最难处理的事情,也许是不能要求普通读者都能欣赏。周作人的文章是写给那些会写文章的人看的,他的那种有点散文家的散文家、美文家的美文家,他的读者不是一般的读者,而是需要有一些学养的读者才会喜欢他的东西。但是并使所有人都喜欢周作人,哪怕是很有文学品味、文学修养的人,出于好多理由可以一点也不喜欢周作人,这一点我非常理解。 我所觉得他好的地方我就讲一点,大家可能都很明白:周作人从“五四”到死都是一以贯之、终生不渝的;他的文字里面有种内在的“张力”。就像我们造桥、造体育馆大顶那样预先要有一种“张力”,因为害怕重力影响就把顶给压下来了,所以要用钢筋从两边拉着。我听说北京的好多奥运体育馆的那个“预应力”、“张力”有100多吨,就准备着那样一种力量在那儿拉着。那么周作人的文字里面也有那么一种“预应力”,有语言的和文学的“预应力”在。这种东西是你看着没什么好的、读着没什么快感的,但是对于中国文章的文学性的贡献非常大。这是什么意义上的呢?就是它的所有“预应力”都针对一种东西,即所谓的“格式化”和体制化倾向,说白了就是种种“俗套”,尤其是那些自命高雅的、唬人的俗套。周作人觉得中国文章最恶俗的地方就是“摇头晃脑”,“摇头晃脑”就写给自己看,自我欣赏。就像鲁迅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里面那个先生背书,到后来连文字都没有了,只有摇头晃脑。周作人说中国文人最恶俗的地方就在这里,写到后来,既没有“意”、也没有“言”、也没有“美”,他就是自己“玩”的那套。跟赌徒斗蛐蛐,或者鬼抽大烟那样,它“上瘾”——中国文章里面最“恶”的趋势是它“上瘾”。就像八股文一样,八股文是一种“瘾”、一种“毒”;它玩物丧志,“玩物”的倾向特别的重。周作人的文章里面的“预应力”就是:防止一切被观念或格式带走的倾向。所以他就写一些那种读上去淡到不能再淡、散到不能再散的文章。以这个标准,鲁迅也是不能免俗的,因为鲁迅的文笔经常被一种诗意的悲情或理想的激动带走,写着写着就低吟或高歌起来。所以周作人也反对“思想家”的文字,虽然他自己在《新青年》时代也是思想斗士。但作为文章来讲他是不喜欢“载道”的。周作人在文字层面极具戒心,非常“狡猾”,他大概也不可能真“献身于”某种思想。“文如其人”,那个人就是要对所有让他“上套的”东西都有所拒绝。文章也是这样,对所有的观念都有所取舍。第二,是对所有的继承的、既有的、被接受的形式都要有所拒绝。周作人是余秋雨式散文的“解药”,这种文章被周作人三下两下就给批得体无完肤,全是“大恶手”,就像下围棋布局里面讲的“大俗手”。然后,第三——他是“五四”作家里面唯一的——他要“反音乐性”,大家记得吗?当时无论是“文言合一”也好、“口语化”也好、“大众文化”也好,要上升到口语表达,周作人连口语都不相信。你说到那种要“唱”起来的那种,那么就完了。真的好文章是拒绝一切“陷阱”——“美”的陷阱,连“美”本身都能变成一种俗套,变成“唱腔”的一种。鲁迅不是《南腔北调集》里面嘲弄当时的文学青年,什么事情都一知半解,只学了一身“文艺腔”——周作人的文章是反所有的“腔”,是“无腔写作”的激进试验。当然到后来你可以说他是“知堂腔”、“苦雨斋腔”、“苦茶腔”,他当然也脱不出“腔”和“调”,但那是“反腔的腔”和“反调的调”。小品文最后也变成某种体制化的东西,一种俗套,但这不是周作人的初衷。在文字层面上周作人文笔之老到,我是很服气的。我们写文章一落笔就知道,不是落入这个俗套就是落入那个俗套——不是落入文以载道的套路,就是落入诗言志的套路;不是落入“分析哲学”的套路,就是落入“现象学”的套路;不是落入西化的套路,就是落入传统的套路——就是你无逃于天地之间。周作人就是活在一个无处可逃的世界里面却想要逃掉的人,可是最后也没有逃掉,所以最后说他是一个“悲剧”也是在这个意义上而言。他已经是聪明得不能再聪明、狡猾得不能再狡猾、怀疑到不能再怀疑,自恋到不能再自恋、自私到不能再自私,竟然最后还是“落水”,栽了一个更大的跟头,用鲁迅的话是“掉到了地上最不干净的地方去”,做了汉奸。但在他三十年代的文字里面,我们能感觉到那种真正的文学性紧张,无声的,看似松弛、闲适恬淡的紧张。他也有一些很从容、很愉快、甚至有点很丰裕的文章,那是读得非常舒服的。周作人的有些文章读得真是舒服,没有一点做作的东西在。周作人的文章不会让人起鸡皮疙瘩。因为他内部的有这个“设置”——他“反”那些东西。包括他的读书摘,也是。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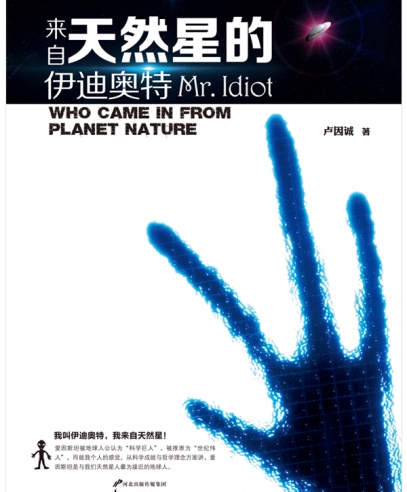
 京公网安备11010202007521号
京公网安备11010202007521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