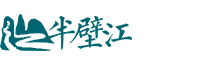序言:短篇小说让我们对文学更放心
时间:2012-01-10 17:53来源:半壁江原创中文网 作者:贺绍俊 点击:
次
阅读2011年的短篇小说,经常能发现一些不太熟悉的名字,这是最令我欣喜的事情。与这一欣喜事情相伴随的是,一些好小说都出自年轻作家之手,这真是喜上加喜。为什么我特别看重这一点,因为这不仅关系到短篇小说写作的后继有人,而且也关系到纯文学性的小说能
|
阅读2011年的短篇小说,经常能发现一些不太熟悉的名字,这是最令我欣喜的事情。与这一欣喜事情相伴随的是,一些好小说都出自年轻作家之手,这真是喜上加喜。为什么我特别看重这一点,因为这不仅关系到短篇小说写作的后继有人,而且也关系到纯文学性的小说能不能存在下去。我们一般将小说分为长篇小说、中篇小说和短篇小说,在我看来,短篇小说是最具文学性的小说样式。现代的短篇小说从“五四”写起,一直写到二十一世纪,经历了一个世纪的反复磨炼,应该说已经成为一个相当成熟的文体了。二十一世纪前后出现了一系列的社会的和文化的变革,比如市场经济、互联网、建立在高科技基础上的新媒体,等等,这些变革对文学的冲击不容低估。但唯有短篇小说似乎在这些外来的冲击下显得无动于衷。这说明短篇小说这一文体已经成熟为一个相当坚固的堡垒,它代表了传统小说的审美形态,不会去迎合外在的变化。为了适应新的文学生产环境,许多文学样式不得不改头换面,而改来改去无非是两种方式,一是把许多适应当下消费时代的新因素强行往文学里面塞,二是把传统意义上的文学性尽可能地淡化。但文学为了适应消费时代的改变,带来的并不是文学的新生,而是文学的泛化、矮化和俗化。当然,以达尔文主义来看这些会是一个乐观的结论,因为优胜劣汰,旧的文学死亡了,会诞生一个新的文学形态,比如网络文学、手机文学。但我始终认为,文化和文学拒绝进化论。因此,能够将一种传统的文学形态保存完好,将是人类文明的幸事。在小说样式中,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都具有“叛变”的可能性,因为它们可以完全依赖故事性而存在。特别是长篇小说,它在网络上,被改造成类型小说,成为了网络文学最红火的样式。网络是一个巨大的文化恐龙,但凡短篇小说这种样式有一点点被改造的可能性,也不会被网络放过的。但至今网络对短篇小说仍是不屑一顾。因此,那些追逐市场、追逐娱乐、追逐新的审美时尚的作家是不会对写短篇小说感兴趣的。也许可以将短篇小说当成一块试金石,测试出一个作家是否真正怀有纯文学的理想。而且,只要还有作家在坚持写作短篇小说,我们也就可以放心地说,文学不会死去。如今,仍有年轻的一代加入到短篇小说写作中来,对于文学来说,不是一件非常值得庆贺的事情吗?
在我所选的二十余则短篇小说里,就有十四位作家是“70后”或“80后”,竟然超过了百分之五十。这里不排除我选稿时带有一点偏向,但我可以肯定地说,他们的这些作品放在年度的短篇小说中绝对是经得起比较的,也是可圈可点的。首先,我从他们的小说中看到了年轻一代的大境界。如畀愚的《我的1991》,看上去作者写的是非常个人化的小事——小说以第一人称的方式,写一个中国人在1991年到苏联做生意的经历。主人公的生意做得很成功,他遇见了一位神秘的苏联人伊万,伊万肯定有很强大的背景,因为他做的是军火生意。苏联人看来非常信任主人公,要介绍主人公与他的上司瓦西里见面。于是主人公带着他的女翻译——一位苏联姑娘娜拉塔莎去了莫斯科。麻烦的是,主人公似乎爱上了娜拉塔莎,他到了莫斯科后,都顾不上联络他的生意,而是每天与娜拉塔莎缠绵在温柔之乡。但主人公与情人在宾馆里缠绵时,窗外正在发生一桩影响世界的历史事件:导致苏联解体的群众示威。是的,作者并不是要在此做一篇宏大叙事,他在小说的一开始就对此作了撇清:一个巨大的帝国一夜之间解体,主人公反而感到高兴,因为他的客户从原来的一个国家一下变成了十五个。小说的最后,主人公还从这桩政治大事件中发现了重大的商机,因为伴随着苏联解体,莫斯科到处矗立的铜像纷纷被拆除,主人公打算用购买废铜烂铁的价钱来收购这些铜像。瓦西里很爽快地答应了,但主人公请求瓦西里帮他找回失踪了的爱人娜拉塔莎时却被拒绝了,这时主人公才发现,他的爱人是克格勃安插的人。作者在叙述中始终要营造一种逃离宏大叙事的气氛,主人公面对红场上和大街上的军车与坦克无动于衷,他也顾不上政府的戒严令,四处去寻找失踪的爱人。但小说的结局颠覆了作者精心营造的气氛:这个似乎与苏联解体毫不搭界的主人公,其生活轨迹实际上从来都没有超出宏大叙事之外。艾玛的《在金角湾谈起故乡》,分明是一个公共知识分子的自白。主人公M女士是一位研究生物学的学者,她的专业也是与现实问题紧密相连的,因此她从专业的角度对人类的现实困境充满着忧患。但这位充满忧患意识的专家却对现实生活中的实际问题束手无策,这并不是专家的无能,而是专家不愿意去效仿和学习现实中的行为规则,因为这些现实中的行为规则是与她的理想相背离的。现实与理想的背离,是所有知识分子共同面对的困惑。作者以故乡这个意象来隐喻这个困惑,这恰是这篇小说的主题之“大”。其次,我也看到了年轻一代的精神困惑。弋舟的《安静的先生》是一篇很耐人寻味的小说。一位退休后的老先生,决心寻求一种淡泊清静的生活。他做一只候鸟,冬天时从北方来到南方,寻一个小城镇住下来,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安静地度日,无所牵挂,也与世事无关。但世事偏偏不放过这个无所牵挂的老头,频频地来骚扰他。作者笔下的老先生,曾经身居要职,显然历经沧桑,这一切作者都没有交代,也无须交代,重要的是,这位老人觉悟到安静才是人生的最高境界。但我以为,作者真正的用意并非要塑造一位安静的老先生,从字里行间,我们分明感觉到作者对现实的激愤之情。社会是那样的喧嚣、浮躁、无序,而人的心境则充满了污秽的尘土,找不到半点洁净之处。安静的先生在同里古镇遇见一位老先生,两人“一见钟情”,心心相印,安静的先生就在老先生的相邀下住在他的家里。他们相安无事,但他们的晚辈却惊慌诧异。作者通过这样的细节表达出年轻一代的自责,也表达了他对这个喧嚣世界的深深困惑。郑小驴的《少儿不宜》,以一个少年的眼睛去看待乡村文明遭遇城市化的野蛮入侵。游离和众多的乡村少年一样,读书的目的就是为了考上大学,离开乡村,进入城市,可是进入城市就能有前途吗?游离的表哥却提供了一个反面的实例。在游离家乡,盖起了一座温泉度假村。虽然游离还没有进入城市,却通过这个温泉度假村感知到了城市的另一面。这让他对未来更加迷茫。这篇小说非常真实地表达了一个“80后”的内心困惑。作者郑小驴就是一位从乡村走出来的作家,他目睹了中国社会近几十年来的巨变,可贵的是他始终带着一种质疑和困惑去面对世界,这也就会使他在文学上走得更远。再次,从年轻作家的作品中我也看到了年轻人的朝气和风格,比如甫跃辉的《骤风》中的一种特别的想象,颜歌的《悲剧剧场》中的青春体的语言叙述,徐则臣的《轮子是圆的》中体现出的一种叙事的冲击力,都带有年轻一代鲜明的印记。这一切也说明一个事实:尽管短篇小说这种形态是非常传统的,但它丝毫也不会是衰老和陈旧的。
短篇小说考验作家观察世界和认识世界的能力。这些短篇小说大概也可以证明,当代作家面对纷繁的世界变得越来越清醒,也越来越成熟。范小青的《我们的会场》是一篇冷幽默式的作品,会场已经成为当代政治、文化的一种基本元素,对于无休无止的大大小小的各种会议,人们多半都见怪不怪。作者本人在生活中肯定是经常要出入各种会场的,但她能够以作家冷峻的眼光去观察会场,发现常态下的荒诞性。刘庆邦的《月光下的芝麻地》写了一个老掉牙的故事。他写的是“文革”以前农村人民公社制度下,一群年轻妇女表现积极性,争做无名英雄,在队里准备收割芝麻之前,抢先悄悄地把芝麻都收了的故事。过去的小说中不乏这样的故事,套路也基本一样,主题也基本一样,无非是要表现人们的集体主义的精神、无私奉献的精神。但刘庆邦却能在这样一个老掉牙的故事上翻唱新曲,并唱出新颖别致的韵味来。我以为这取决于作家观察世界和认识世界的方式。过去热衷于讲这类故事,是受制于当时的政治意识形态,在意识形态化的文学思维中,它逐渐定型为一种争当劳模、先进和热爱集体的叙述模式。刘庆邦是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作家,那个年代的生活经历是他一笔丰富的写作资源。但我敢断言,他当年的创作也曾受到那个年代特定文学思维的掣肘,这妨碍了他开掘这笔丰富的写作资源。但可贵的是,刘庆邦并没有在这笔写作资源上形成顽固的思维定式,相反他能从一个崭新的角度去重新整理以往的经验。他从这个故事中获得了一种劳动的幸福感,他带着这种幸福感来讲述故事,这种劳动又是与大自然连在一起,大自然的美与劳动的幸福感交织在一起,构成了这篇小说的和谐乐章。
我还特意选入了一组劳马的小说。严格说来,劳马的小说应该归入微型小说。微型小说与短篇小说的区分主要在于篇幅的长短,但篇幅的长短会带来审美形态的不同,所以一般我们会把微型小说和短篇小说看成是两种小说类型。但它们之间的界限不是壁垒森严的,实际上相互之间有渗透,有交错。我看重劳马小说的特别意义。我更倾向于把劳马的小说称之为一种哲学小说。当然提到哲学小说,我们很容易地就想到法国作家狄德罗的《拉摩的侄儿》,这位法国启蒙时代“百科全书派”的代表性人物大胆地采用小说文体来阐释他的哲学观点,宣扬他的政治主张。尽管这部小说被恩格斯称赞为“辩证法的杰作”,尽管黑格尔被其中的辩证谈吐所折服,但这样一种以小说的形象瓶子盛哲学的抽象浓汤的做法并没有流行开来。虽然哲学小说一直并没有形成阵势,但现代小说的发展趋势之一便是小说不断地向哲学靠近,例如卡夫卡、贡布罗维茨、布洛赫、穆齐尔等作家,在他们的小说中哲学意蕴非常突出,他们以哲学的方式进行思考,接纳可被思考的一切,拓宽了小说的主题,使小说与哲学相接近。即使嘲讽过《恶心》的昆德拉也并不遮掩他对哲学的兴趣,他的小说处处闪烁着哲学的睿智。中国当代小说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有一次向西方现代文学靠拢的高潮期,在这个高潮期,当代的作家也尝试着开启哲学的思路。这典型地体现在“寻根文学”上面。很可惜,到九十年代以后,在物质主义和欲望化潮流的冲击下,作家们疯狂地奔向形而下,刚刚开启的哲学思路就这么中止了。而我是在这个意义上将劳马的小说称之为哲学小说的。也就是说,它呼应着西方现代小说的发展趋势,从哲学的门径进入小说,重新点燃了中国当代小说的哲学火炬,使八十年代在“寻根文学”中表现出的哲学智慧重新焕发出光彩,让我们看到了小说摆脱形而下泥淖的希望。因此尽管劳马的小说不能说是严格意义上的哲学小说,但他的小说对于中国当下小说的现实意义却在于哲学,他的小说提醒我们,中国当下小说最缺失的是哲学。
还得为裘山山的《打平伙》做一点说明。这篇小说语言生动,情节曲折,看似很随意地讲述一个老牛啃嫩草的故事,却在不动声色之中善意地批评了老董。裘山山是一位始终对历史和长辈怀有敬意的作家,她十分珍惜岁月留下的精华,这构成了她的文学叙述的基本特点。《打平伙》当然算得上是一篇短篇佳作,但这篇作品很容易被人们忽略,因为它是发表在年终最后一期《西湖》上的。现在每年好几家出版社会组织出版多种年度的小说选,但出于市场发行的考虑,年度的小说选往往在一年还没有结束时就编好了,于是年底最后一期文学刊物上发表的小说,基本上就成为了这些年度小说选无法关注到的盲点。我希望我参与编选的年度短篇小说选能够消除这个盲点,因而也就将上一年度最后一期的刊物纳入到选编的范围,相信读者们也会同意我的主张的。也正是在这样的主张下,《打平伙》这篇佳作进入到了我的视野中。只要贵州人民出版社继续将这个年度小说选做下去,我们就仍然以这样的方式消除我们的编选盲点,以保证每一篇佳作不会被遗漏。
(责任编辑:冷得像风) |
------分隔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