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人长期从事公安题材文学(以下简称“公安文学”)研究,对涉警题材文学作品也有所涉猎。在我所细读过的纯文学作品,即大型纯文学期刊(包括一些单行本),如《人民文学》《当代》《收获》《钟山》等所刊发的作品中,发现50%以上系涉警题材,也就是说多多少少有人民警察在其间活动,而且这些警察形象大都不怎么好,让人看了心寒、心酸、心颤,从而让读者对公平正义失望,甚至会对“中国梦”产生怀疑。 2013年12月,中宣部与中国作协等五部门联合发出通知,开展以“中国梦”为主题的文艺创作活动。在实现“中国梦”的进程中,文学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宣传好中国形象,已成为作家、评论家和文学工作者达成的共识。但是,我发现目前相当多的涉警题材文学作品没有讲好中国故事,没有传播好中国声音,作品中的警察故事与现实严重不符,与“中国梦”有相当差距,所有这些负面警察形象并不能带给读者信心、力量和鼓舞,不能提振国民精气神,不能让读者对人民警察产生尊敬之感、同情之心、理解之意。作家们笔下警察形象为何与现实中的警察形象相差甚远,原因何在?窃以为,作家们没有放下身段(放下架子)、深入警营了解警察生活,才会导致不了解人民警察、不懂公安工作、不知悉办案程序,最终才将人民警察写得不够真实,将办案程序整得漏洞百出。如此写作,将不利于构建和谐的警民关系,不利于社会的安全稳定。 以东方学为研究对象的萨义德认为东方学作为一种话语,是欧洲文化霸权的产物。东方并不是实在的东方,它是被西方话语创造出来的“他者”,它是被西方话语想象性地虚构出来的谎言。东方学隐含的前提是:因为你是东方人,所以你有罪,所以你是低人一等的。在西方人心目中,东方形象是和神秘、愚昧、腐朽、纵欲、罪恶等本性联系在一起的。我看了如此多的涉警题材作品,得出一个结论:大多数非公安系统的作家们心目中的人民警察形象就是一个“他者”,犹如西方人心目中“东方形象”一样,非常不真实。如果这些涉警题材(所谓名家名篇)被译到国外,正好迎合了西方人想象中的“东方形象”,正好被西方敌对势力所利用。尤其是在大力倡导意识形态安全的当下,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加紧对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实施多层面的文化侵略,以实现其“和平演变”的战略图谋。因此,有民族责任感的文艺工作者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形象及中国警察形象的重要性,必须提防文化殖民主义,用心用情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宣传好中国警察形象。 著名诗人艾青认为:“任何艺术,从它最根本的意义上说,都是宣传,也只有不叛离‘宣传’,艺术才得到了它的社会价值。”且看一些名家名篇(小说)是如何“宣传”人民警察的。如中篇小说《第四十圈》中的部分原文:“那个人(人民警察)慢慢地逼近她(牛光荣),从他嘴里冒出的混合着酒精、烟草和其他说不出来的怪味道喷在她脸上,‘现在摆着你面前的只有两条出路,要想保住你自己,就必须承认是齐光禄强奸了你,而不是你自觉自愿的与他发生性关系;要想保住齐光禄,你就得承认自己是卖淫,包括与齐光禄和其他男人发生性关系,都是你自己主动勾引他们的。”又如,“当时你们劳教光荣的时候是怎么说的?难道连你们公安说话也不算话了吗?”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是政法工作的核心价值追求,种种迹象表明此作在彰显公平正义这一主题内涵方面是大大的失败。再如,“‘滚出去!’办案人员怒不可遏,一拍桌子站了起来。”……上述场景、细节、情节、叙述、描写等严重地损害了人民警察形象,严重地伤害了那些信念坚定、兢兢业业、无私奉献的人民警察和英烈家属的情感。福克纳说:“好的小说让人想起人类昔日的光荣、勇气、荣誉、希望、骄傲、自信心、同情心、慈悲心、牺牲精神,藉以鼓舞人心,使人增加忍受苦难的能力。”很明显,《第四十圈》称不上是优秀的小说,因为它并不能提振人民警察的精气神,甚至有可能会起到反作用。 《第四十圈》发表在《人民文学》2014年第2期头条,紧接着被《小说月报》2014年第4期、《中华文学选刊》2014年第4期、《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 》2014第3期和《小说选刊》2014年第4期等大刊名刊转载,足见此作的影响力,人民警察的负面形象也会大大地被传播。 实际上,不仅仅是《第四十圈》中的人民警察形象被歪曲、被解构,现在全国相当多的名家笔下和名篇中的人民警察形象都走了样、变了味,与现实大相径庭。这些警察要么对群众态度粗暴,恶语相向;要么胡乱执法,“不作为”或“乱作为”。在大力推行阳光执法的今天,在人人都是录音机、人人都是照像机、人人都是麦克风的当下,特别是刑事诉讼法于2011年进行第二次大修之后,新刑事诉讼法第121条规定:“侦查人员在讯问犯罪嫌疑人的时候,可以对讯问过程进行录音或者录像;对于可能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的案件或者其他重大犯罪案件,应当对讯问过程进行录音或者录像;录音或者录像应当全程进行,保持完整性”。人民警察在执法过程中肯定会珍惜自己的“饭碗”和前途,一定不会“胡搞”,根本就不可能出现以下作品所描述的样子: 如长篇小说《高兴》(作家出版社2007年9月)中的孟夷纯到城里的目的是为了挣钱。她将出卖肉体,用屈辱和泪水换来的钱寄回老家,给老家的警察做缉捕杀死她哥哥凶手的办案经费。她每隔一段时间就寄一次钱,每一次金额成千上万。警察拿了饱含她血泪的钱,南下北上,却一次一次让她失望,没有结果。 尽管小说《高兴》震颤人心,却不能慰藉读者心灵。台湾作家陈映真说:“文学是使绝望丧志的人重新点燃希望的火花,使扑倒的人再起,使受凌辱的人找回尊严”,小说《高兴》恐怕不能产生上述效果。 小说《高兴》的作者大名如雷贯耳,他竟将人民卫士想像成这个样子,其示范效应和名家效应不可小视!读者读了《高兴》,怎么能“高兴”得起来呢?他们只会对行使公平正义的人民警察顿生反感,同时也会对国家机器大失所望。 长篇小说《愤怒》(团结出版社2004年10月)中李百义的妹妹来到城市,渴望能凭自己的劳动过上另一种生活,但她被收容站“收容”,遭强暴,被逼卖淫。李百义“愤怒”了,他不相信在这阳光灿烂的地上,讨不到一个说法。于是他与父亲开始了漫长的上访之路,但以钱家明为首的警察出于阻止他们上访的目的而将年老体弱的父亲打死,继而谎称其失踪。 ……,…… 类似上述单行本中的负面警察形象还有很多,尤其是“官场文学”中的负面警察形象更多,不再一一列举(国家太大,文本太多),接着再看大型纯文学期刊中的警察形象(下文仅以中、短篇小说或小小说为例),如《早晨响起的门铃声》(《钟山》2010年6期)中公安局长老肖是人民警察中的败类。一是他变相地收受贿赂,老吴和老陈打牌给他送钱,他一场就赢了9千多。不久,老吴的舅子——一个山区派出所民警就调进了城关派出所。二是玩女人不择手腕,与张姓女娃子颠鸾倒凤…… 《谁能让我害羞》(《长城》2002年第3期、《新华文摘》2002年第8期)中本来是一个由乡下来到城市的送水少年与一个中产阶级主妇发生了悲剧性误解,却被作为权力象征的警察错误地将少年的情绪冲动定性为“入室抢劫”。 ……,…… 还是回到《第四十圈》小说中来看牛光荣怎么了?她“被锁在铁笼子里。这是一间囚室。”“齐光禄被塞进一辆黑色囚车。”如此叙述,说明邵丽真的不懂公安工作,不了解办案程序,不知道刑事讼诉法已经修改了。派出所里从来就没有设过囚室,以前叫“留置室”,后来改为“讯问室”,更没有“囚车”这一说法。 《谁能让我害羞》、《请勿谈论庄天海》(《收获》2013年第1期)和《天火》(《当代》2013年第5期)中只有一个人民警察在执法办案,这完全不符合办案程序…… ……,…… 上述名家名作名篇都是在隐性地宣传人民警察的负面形象,上述作者都是名人,作品都是名篇,刊物都是名刊,名刊、名人、名作效应会使警察的负面形象影响呈几何级数递增,可怕,真的非常可怕! 也许有的作家说:我的作品并不是现实生活的反映,只是现实生活的隐喻。美国批评家杰弗里•哈特曼也说:一切语言都是隐喻性的和象征性的,即必须依赖隐喻和象征来完成“意义”的传达。诚然,上述作品中有一些使用了隐喻的写作手法,把人民警察只是作为道具,作为符号。但是,借人民警察来说事,或把人民警察当作噱头,也是不妥的。毕竟,人民警察是国家形象的代表。 我还发现一条规律,即创作上述作品的作家都不是公安系统的人民警察。为什么这些作家笔下的人民警察被矮化、被丑化、被歪曲呢?个中原因非常复杂,三言两语难说清。 事实上,也有一些非公安系统作家笔下的警察形象比较真实,比较靠谱,也就是说写好了普通的人民警察。这些作家对人民警察的态度基本上是持隐性的颂扬立场,虽然其笔下的小说与主流意识保持一定的张力,但这些小说依然能滋润心田、照亮人心。 如非公安系统作家张笑天的《山地车》(2008年7月5日《光明日报》第6版)讲警察如何人性化执法,如何为构建和谐社会而尽心尽责。小说中的“我”是一名父亲,生活艰辛。女儿考上了重点中学,必须买一辆自行车。“我”便到废品收购站买了一辆旧车,却被人“借”走了。有人“点拨”我也去“借”一辆。正当我下手时被警察逮现行,我当即给警察跪下,请求他们别告诉我女儿说我当小偷被拘留,不为给我留脸面,只求给孩子留个做人的尊严。警察还真的答应了我的请求,不仅将我偷车的事情隐瞒,还集资为我女儿买了一辆车。我以为,像这样的作品就能启迪人心、温暖心灵。 上文提及的小说《谁能让我害羞》不是现实生活的反映,而是现实生活的隐喻。但是,为什么此文就不能像《山地车》那样增加一些人民警察人性化执法的部分呢?鲁迅在《呐喊自序》中说:为“别人设想”,“删削些黑暗,装点些欢容,使作品比较的显出若干亮色”“但既然是呐喊,则当然须听将令的了,所以我往往不恤用了曲笔,在《药》的瑜儿的坟上平空添上一个花环,在《明天》里也不叙单四嫂子竟没有做到看见儿子的梦,因为那时的主将是不主张消极的。”如果《谁能让我害羞》中的女主人公后来良心发现,向人民警察为送水工求情,是不是温暖许多呢?人民警察则顺势人性化执法——不处罚那名送水工,那么,这一点亮色则能抚慰众多读者的心灵。 再看邓宏顺的《归案》(《湖南文学》2012年第11期、《小说选刊》第12期)中的陈副大队长坚决主张帮杀人嫌疑犯李泽洲讨回工钱。其理由是:“嫌疑犯犯了法,该当的罪他必须当,但他的正当权益也应当受到保护!我总觉得我们有责任帮他讨回这笔工钱!”在警察的帮助下,李泽洲讨回了工钱,服服贴贴地跟着警察走。小说又突转,遭遇了泥石流,李泽洲妻子怂恿只伤皮相的他趁机逃跑,他却说:“如果换两个我不很佩服的公安人员,现在我肯定会逃跑……但他俩却冒着那么大风险为我讨要工钱……我要等到毛队和陈副来找我。”由此可见,李泽洲已经被警察的行为感化了。用李泽洲自己的话来说:是警察帮他讨回了人格和尊严。 ……,…… 以上所列举的出自非公安系统作家之手的公安文学作品恰到好处地构建了人民警察形象,彰显了人民警察核心价值观,值得大力宣传。 本人研究公安文学达10多年之久,倒是发现相当多的出自公安系统作家笔下的人民警察形象是正面的,与现实生活相符合。据我分析,毕竟公安作家自身就是人民警察,当他们潜心沉浸到自己作品中之后,潜意识地会对人民警察产生一种归属感、认同感、亲近感。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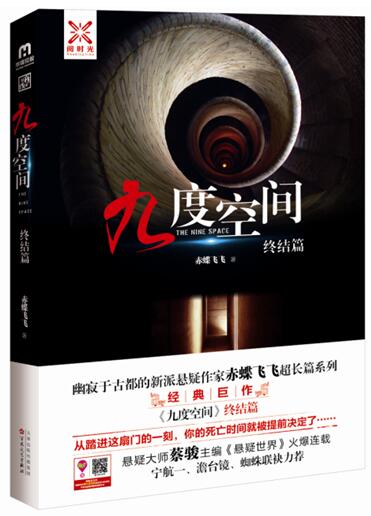
 京公网安备11010202007521号
京公网安备11010202007521号